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 二○二○年增訂版 | 生病了怎麼辦 - 2024年11月

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 二○二○年增訂版
讓女人的二二八經驗被看到,
讓影響及定位台灣歷史的二二八事件,
有女人發出的聲音;
也從這些堅毅台灣女人的生命經驗中,
得到力量、習得勇氣,不讓國家暴力再發生。
一本關於女人的二二八經驗,突顯了性別和政治、歷史間相互交織複雜的現象。
作者以生命史的方式來記錄這些因二二八政治屠殺事件,而變成寡婦的女人的生命悲劇,從活下來的女人的親身經驗來論述「女性與二二八」的關係。
這些聲音的出現,使得女性悲憤的一生,苦難的命運,以及無可湮滅的衝擊與傷害,終於得以自主於二二八傳統男人論述之外。
本書初版於一九九七年,經過二十三年的時光,書中所訪談的二二八寡婦早已陸續辭世,二二八議題的書寫也已擴及於各個面相,因此,在二○二○年增訂版中,除了原有的內容之外,作者沈秀華教授增加了新版序,也補進了〈受害家屬的受暴主體性〉,更深入地從受害者家屬的角度,剖析施暴者與受暴者之間的關係。期許增訂版的出版,不只是讓女人發聲,也要讓更多人從書中這些堅毅台灣女人的生命經驗中得到力量,習得勇氣,守護民主,不讓國家暴力再發生。
作者簡介
沈秀華
任教於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研究領域:性別、移民、親密關係、認同政治
相關著作:噶瑪蘭二二八
新版序:向二二八查某人學習 沈秀華
自序:讓政治寡婦的聲音發諸於世 沈秀華
緒論1:受害家屬的受暴主體性
緒論2:查某人的二二八
開木屐工廠的守寡母親(郭一琴)
艱苦扶孤的警察太太(黃碧珠)
對天呼喚的副站長夫人(蘇白勉)
人亡,人情亡的體驗(楊𤆬治)
踏浪的人生
細姨ㄚ環的悲情歲月(潘罔)
撿蕃薯度日的查某人(王鄭阿妹)
旅社頭家娘的冤情(盧陳碧水)
從二二八走過來的歲月(許江春)
從醫生娘到農夫的艱苦歷程(張玉蟬)
不被二二八打倒的堅強女性(張楊純)
被運命捉弄一生
序
向二二八查某人學習
《查某人的二二八》一書在一九九七年出版,距今已有二十三年,而離一九九二年開始從事書中口述歷史的訪談,更是要近三十年前的事情。
近三十年間,當年書中所訪談的二二八寡婦早已陸續辭世,其中一些人過世時,仍不知當年受害親人的屍骨何在,轉型正義在當時仍是個遙遠的政治議程。二二八寡婦所代表的是有幾個世代的台灣人,以終生承受國家暴力的痛苦及不正義而離世。「我是歹命查某人」可能是不少二二八寡婦在生命臨終時,對自己一生的結語,因為他們所承受的不義終究沒有得到平反撫慰,尤其女人在當年代的社經處境又相當弱勢,他們最後常只能以命運來和緩個人所遭受巨大結構暴力的無奈與無力,甚至有些會自我譴責,自認是個人命不好,才會遭遇如此傷痛。
暴力的可怕與可惡,有在於讓人受害受難後,還要自我承擔起受害的因緣與責任。社會的殘酷,有在於我們可以不去看到別人的受苦受難,何況是已逝去的人所受的痛苦及不正義。在這樣的思路下,就會覺得二二八或白色恐怖已是台灣上世紀的事件,為何我們還要去了解這些歷史?為何還要去平反其所代表的不正義?
因為暴力、尤其是以國家武力及資源所行使的暴力,既來勢洶洶又傷害深遠,絕不會只是歷史,而可能是離我們不遠的進行式。對許多台灣人而言,二○一九年中起所發生的香港反送中抗爭運動中,香港警察對民眾的施暴就是鮮活恐懼的例子;同年智利、伊朗也都有軍警以殘暴行徑打壓各類社會抗爭群眾。
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流血流淚的歷史要告訴我們:如何可以不要重蹈暴力與傷痛!
當許多台灣男人在一九四七年被國民黨殺害或監禁的同時,許多這些男人的妻子與家人也成為二二八最直接的受害者,而且是在漫長的政治戒嚴中受苦、恐懼。《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一書至今仍是少數從性別、日常生活出發,紀錄國家暴力的出版品。二二八寡婦長年的刻骨銘心傷痛,以及他們從痛苦恐懼中奮力生存、讓受傷的自己還成為家人及別人依靠的力量,這讓我們在聆聽或閱讀他們的經驗的同時,既為他們的受害而感到難過與憤怒,也為他們的勇氣與堅毅而深深感動及油然升起敬意。
這本女人的二二八口述歷史經驗,曾讓一些台灣人對二二八和國家暴力產生直接的情感連結:原來那段台灣黑暗的歷史,不再只是歷史,而是有血有肉的日常苦難、生存與抵抗;原來在當前國際局勢快速變動、在中國威脅下,黑暗歷史對台灣人也不一定只是歷史,而是有可能重演。一九九七年第一次出版這本書時,當時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讓女人的二二八經驗被看到,讓影響及定位台灣歷史的二二八事件,有女人發出的聲音。二○二○年再版《查某人的二二八》一書,就不只是要讓女人發聲,而是要讓更多人能從書中這些堅毅的台灣女人的生命經驗中得到力量,讓我們習得勇氣,切記國家暴力的不該,以及守護民主,不讓暴力再發生。
開木屐工廠的守寡母親 郭一琴(屏東市人,現居台南市,其夫葉秋木,屏東議會副議長,二二八受難者) 採訪時間:一九九五年七月一日 採訪地點:台南市葉餘香宅 口述語言:福佬話 我叫郭一琴,民國前四年生,今年(書中口述的今年皆指採訪當年)已經八十八歲。 「一琴」的由來 我祖父少年時,帶伊的老母從大陸來台灣,伊是當時的進士。阮老爸在伊三、四歲時就開始讀冊,冊都這麼大本,阮老爸就一直「唸」冊,古早,冊都嘛用唸的。阮爸爸在伊十二歲時就中秀才,十三歲上榜林,可以去考舉,阮老爸考舉考一冬(一年),寫的文章還是囝仔文,就無考中,再過去,第二年,日本人就來了,變成日本時代,後來阮老爸就去讀日本學校,畢業以後,就去考普通文官,一考就考上。彼時陣我剛出世,所以阮老爸就叫我「一琴」,就是講伊做官要真清廉。古早有一個人做官真清廉,伊要「老」(死)的時,只剩下一個琴和一隻鶴,所以我的名叫郭一琴,乳名叫友鶴。真的,阮老爸做官有夠清廉,伊一考上文官就被派去「阿猴廳」(現今的屏東)做秘書兼通譯,彼時,屏東無高屏大橋,都要坐竹排過溪,水隆隆的,後來才有火車,就比較安全。 我七、八歲就去「阿猴」公學校讀冊,彼時陣,屏東叫「阿猴」。彼時陣和阮老爸,大家生活作伙,感覺真好。我公學校畢業以後,就去讀高雄第一高等女學校,那都是日本人在讀的學校,我是用考試,考進去的。彼時,第一高女不好考,一方面要看家庭,另一方面也要靠實力,我去讀高女是因為我自己要讀冊的,不是因為家庭逼的,我真愛讀冊,也不想輸人,就去考高女。 阮厝的人都真重視教育,我有一個兄哥、三個小弟和一個大姐,除了一個小弟小時就無去(天折)以外,我所有的兄哥和小弟都是醫生,都在屏東開醫生館。我高女讀四冬畢業以後,就去大官公學校教冊,彼時我教一年級、二年級和三年級的學生,什麼都要教,在大官教二年以後,我就轉去黑金公學校再教一年的冊,訂婚以後就辭去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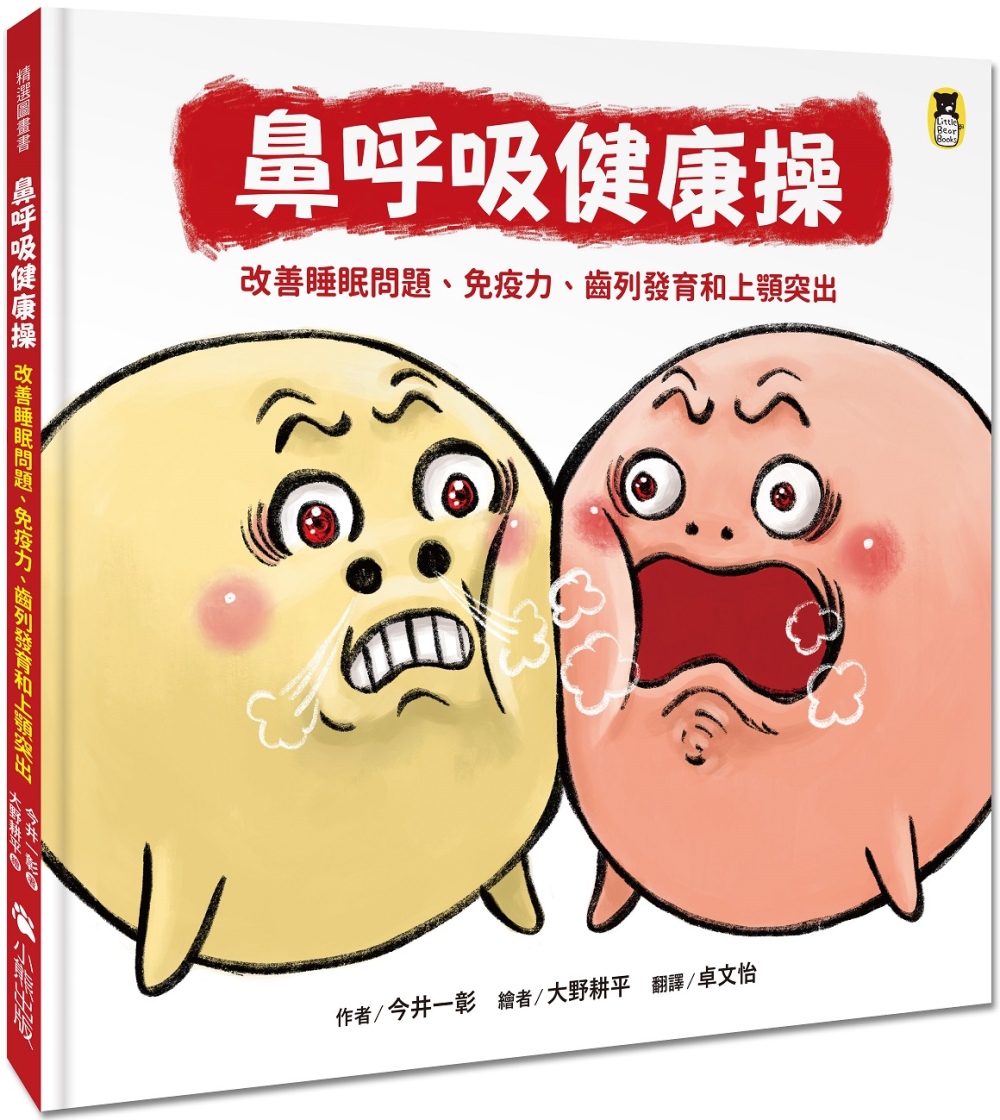 鼻呼吸健康操:改善睡眠問題、免疫力...
鼻呼吸健康操:改善睡眠問題、免疫力... 視覺內容營銷:利用信息圖表、視頻和...
視覺內容營銷:利用信息圖表、視頻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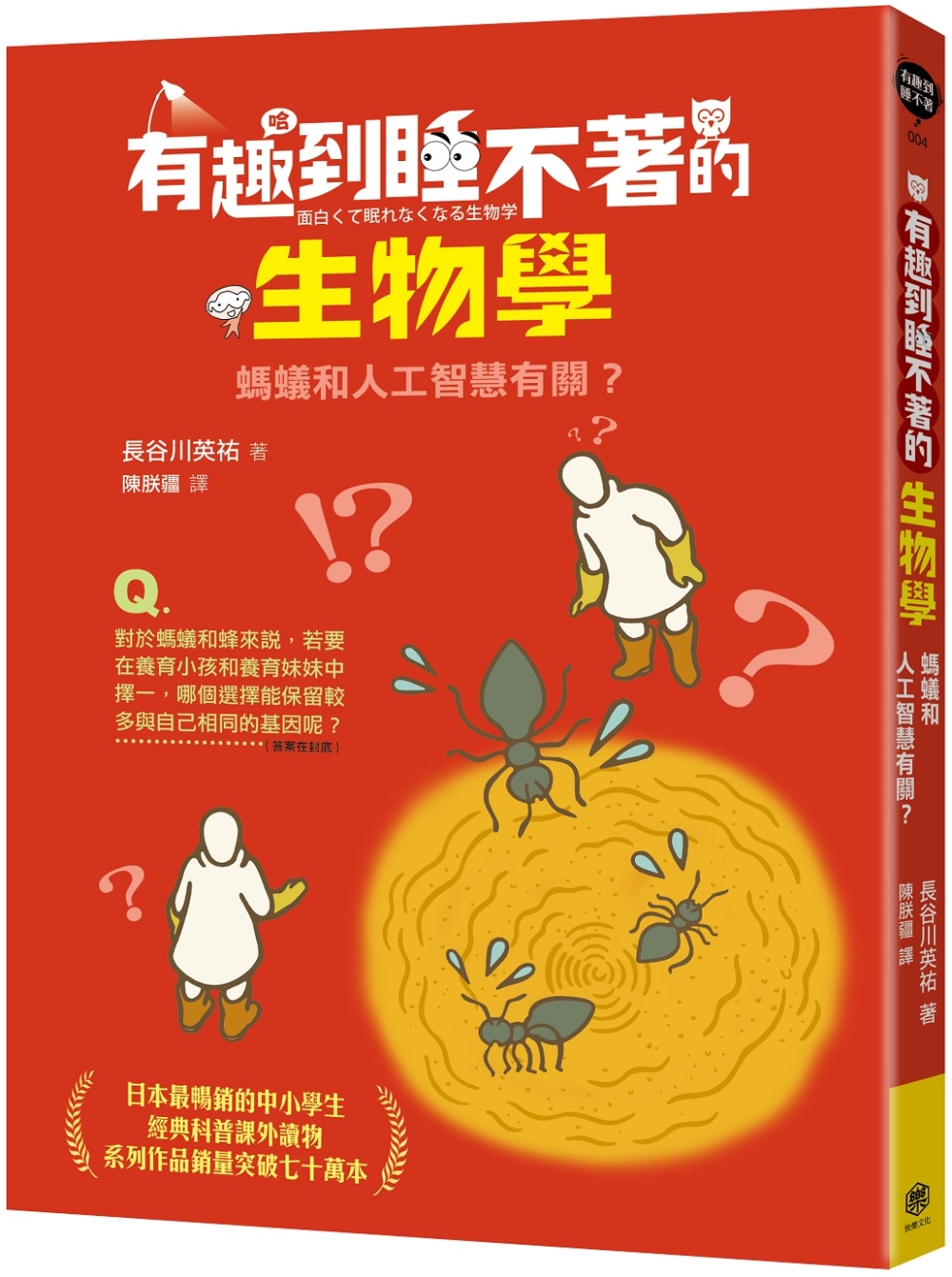 有趣到睡不著的生物學:螞蟻和人工智...
有趣到睡不著的生物學:螞蟻和人工智... 喚醒世界:女性和英勇女性特質經典故事
喚醒世界:女性和英勇女性特質經典故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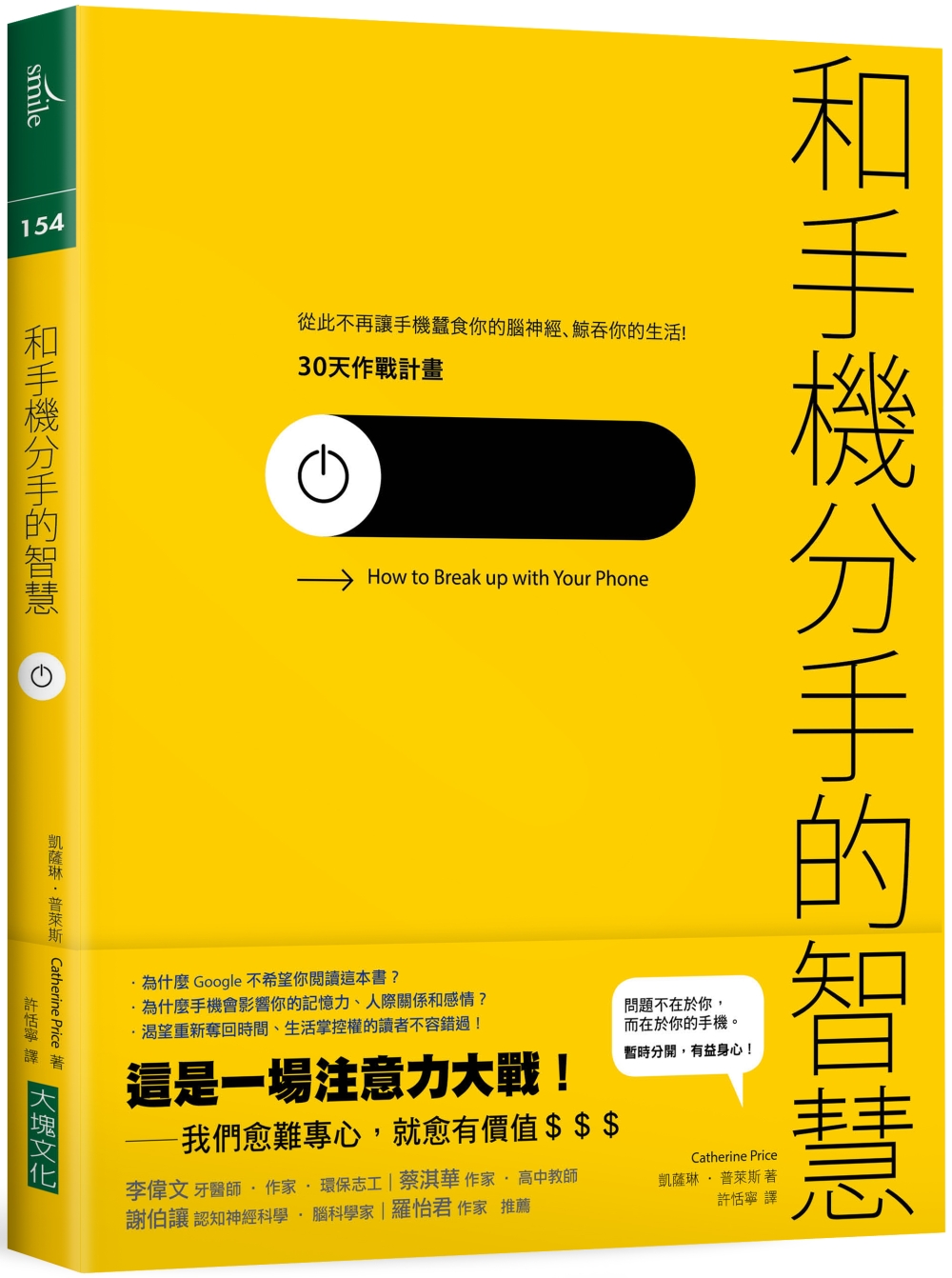 和手機分手的智慧:從此不再讓手機蠶...
和手機分手的智慧:從此不再讓手機蠶... 超刺激的決戰大富翁
超刺激的決戰大富翁 向大自然借點子:看科學家、設計師和...
向大自然借點子:看科學家、設計師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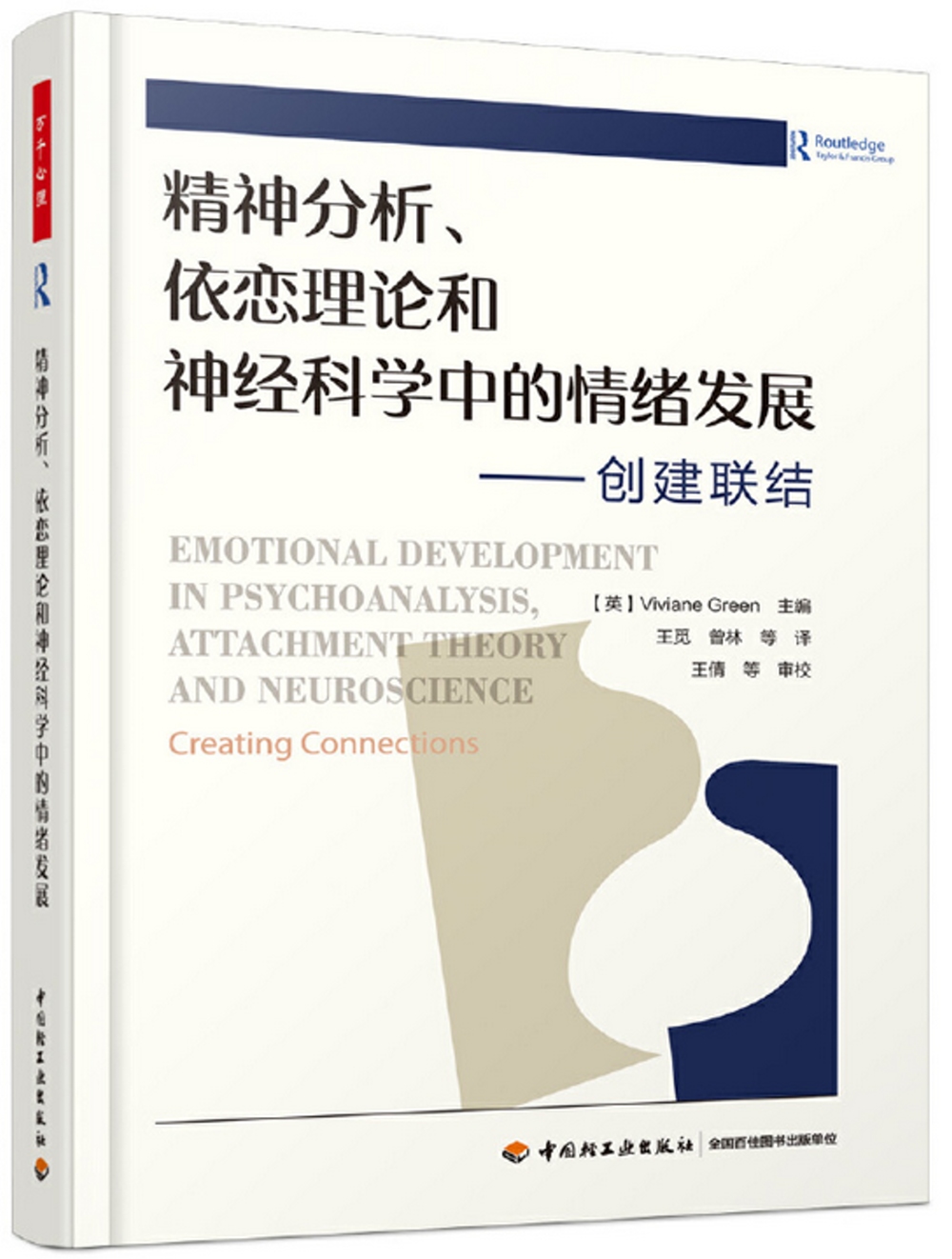 精神分析、依戀理論和神經科學中的情...
精神分析、依戀理論和神經科學中的情... 0歲baby視覺圖卡
0歲baby視覺圖卡 蘭嶼、飛魚、巨人和故事(再版)
蘭嶼、飛魚、巨人和故事(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