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自由傳統 | 生病了怎麼辦 - 2024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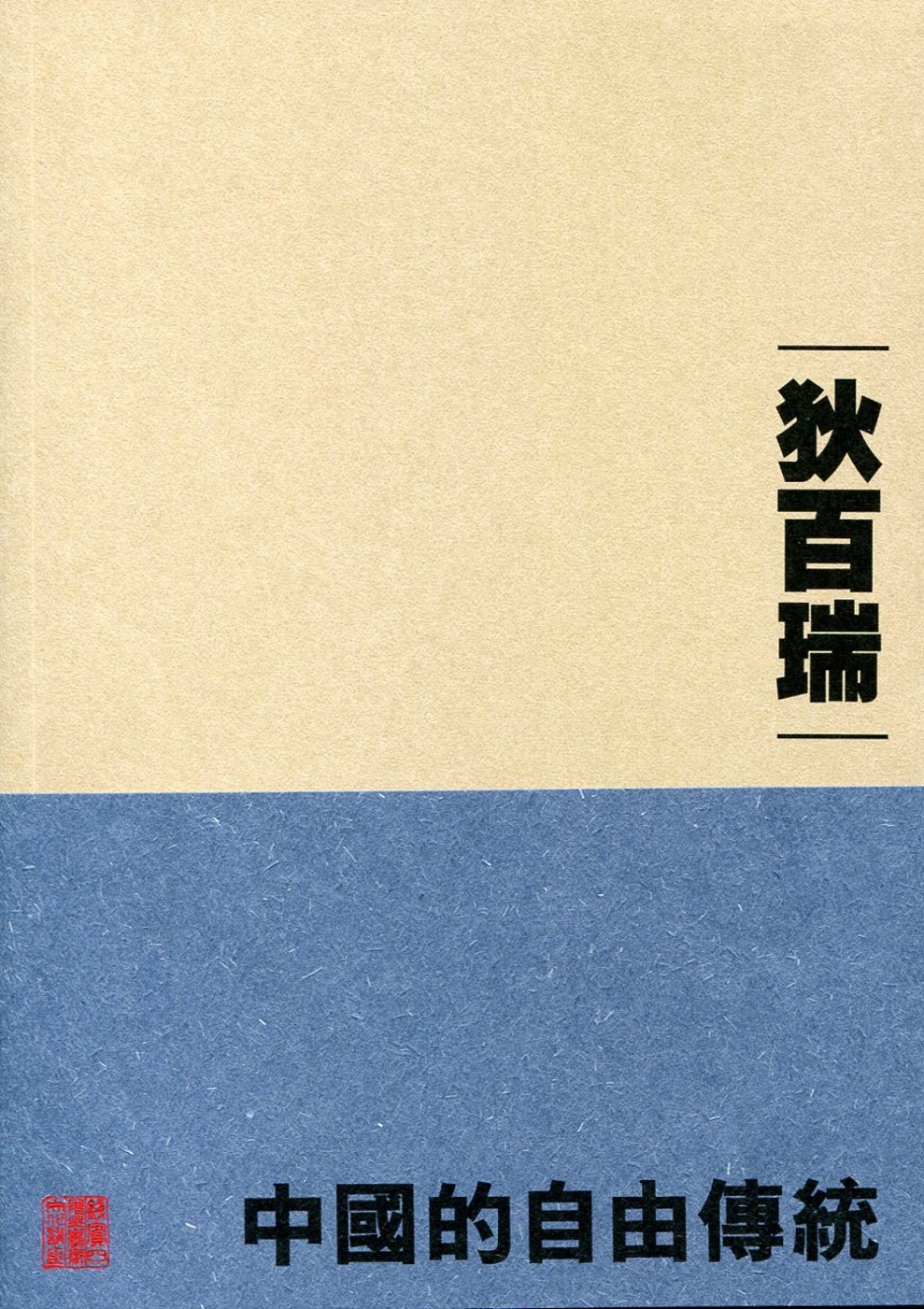
中國的自由傳統
狄百瑞就中心宋明理學的傳統討論中心思想中的自由主義特質。書中論及新儒學「學以為己」的個人自發色彩,其強調自得,相互激勵等價值的教育思想,以及明代知識分子自任於天下的責任感,認為黃宗羲正代表了這種自由主義特質的新綜合。在最後一章中,狄百瑞並討論這種自由思想在當代中國所遭遇的困境。
作者簡介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梅遜講座教授,專研新儒學、東亞思想與宗教,1969年榮膺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會長。他不但是一流的學人,且是一流的教育行政長才。其著述不輟,質量皆富,在50–60年代傾力投入到新儒學之前,編寫了一系列有關東方文化與文明的重要著作,有關出版成為英語世界對中國乃至整個東方思想研究的分水嶺。
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系列總序(金耀基) vii
迎狄百瑞先生來新亞書院講學(金耀基) xiii
譯後贅語(李弘祺) xxv
引言 1
第一講 人之更新與道統 13
第二講 朱熹與自由教育 27
第三講 新儒學思想中的個人主義 57
第四講 明代理學與黃宗羲的自由思想 91
第五講 自由主義的局限 123
引言(節錄)
當我接到邀請承乏1982年度的錢穆講座時,雖然很懷疑我是否能勉孚由中國學術界中這個偉大的名字所激起的期望;但被邀約來參加這個聲譽卓著的講座,這項殊榮本身就足以使我接受了。而且,我也有著強烈的個人理由來承乏這項責任──過去許多年來,錢賓四先生透過他的著作一直是我的老師。雖然其他學者也在這種方式下教導我,但錢先生在引導我研究中國思想上則是為時最早而且影響最深的一位。任何人接到以這樣一位久施教澤的師長為名的邀請時,他當然是不會加以拒絕了。
在我心中錢穆先生傑出的學術貢獻與十七世紀一位學者黃宗羲是結合在一起的。在我開始研究中國文化之後不久,黃宗羲就吸引了我的注意。這已是1937至1938年間的事了,當時大多數人都以為只有從事與傳教工作有關的人才會想研究像中國這麼一個不關緊要的題目。但當時在紐約及哥倫比亞大學,對中國研究的興趣正如同宗教一般,具有政治色彩,我和保羅.羅布森(Paul Robeson)及其他人同學,他們的言論激進,我與他們一樣也同情社會主義,對於毛澤東正在進行的革命鬥爭具有一種年輕人的熱情。後來,當我與同時代的其他人目睹歐洲的變局後,開始有了覺醒──史達林的整肅行動出賣了革命的理想,希特勒與史達林的協定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暴行更形放肆,納粹和蘇聯軍隊宰割了歐洲,四處屠殺猶太人。再又是蘇聯的古拉格群島等等。我對那些主張拿西方式的革命來解決中國困境的辦法就不再那麼樂觀了。我開始探索中國人自己的生活與歷史,也許它能為中國的未來提供一個免於受革命與反動之苦的未來。
在探索的過程中,我注意到了當時尚不為西方世界所熟知的黃宗羲。二十世紀初,黃宗羲是中國變法家及排滿革命家心目中的一個英雄。那些想從中國歷史中尋找民主價值的人稱黃宗羲為「中國的盧梭」,雖然他們很少把黃宗羲的思想與民主價值作深入比較,也很少從黃宗羲的時代背景中詳細分疏他的思想。後來,當「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平地而起,認為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案就是從中國歷史中完全解放出來的時候,革命的浪潮就把他們這種儒家的溫和改革思想沖到一旁了。
就在這個關頭,錢穆先生進入了我的心中。錢先生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的方法為觀察這個蜩螗的時代提供了廣泛的視野。正如錢先生後來在本講座所再度肯定並細加分疏的觀點一樣,中國千萬不應該想要用那種從根拔起並摧毀過去遺產的文化革命的方式來得到解放;它只能透過中國文化本身,不管它的好壞都面對它,認為中國人的未來實植根於中國文化這種方式才能獲得。雖然有些中國人可能寄寓異國,並且吸收不同文化;但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畢竟是生活在由共同的歷史所形成的條件與外觀之下。對他們來說,移民異域當然是不可能的。1
錢穆先生是研究中國思想一位罕見而成就卓越的史學家。錢先生早年曾重新疏解新儒家的史料,並且從宋明及清初思想史的立場來覆按黃宗羲思想的脈絡。我發現錢教授的著作(特別是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期間我在太平洋服役,開始研究黃宗羲自己關於思想史著作的時候。錢教授在其所撰十七至十九世紀思想史的書序中,提醒讀者注意宋代新儒家思想的淵源。2
黃宗羲最膾炙人口的著作《明夷待訪錄》成書於公元1662年,正是他從抗清運動中歸隱不久的時候。在這部批判明代專制政治及其腐化的著作之中,黃宗羲強烈地表達了他在明末參與改革的努力,以及他以明代遺老身分抗清的雙重挫折。作為明朝忠臣,黃宗羲鯁直地批判明廷的缺點來為朝廷盡忠(儒家意義下的盡忠);同時,身為一個對歷史有廣泛認識的新儒家,他對於朝政的敗壞也詳加分析,並遠溯其根源,迄於遠古。
黃宗羲的學術努力可能是近代以前對於中國專制政治所作最整體而有系統的批判。這部書的確對傳統帝制作了激烈的攻擊。雖然黃宗羲痛詆的是政府,但是繼起的清朝卻也覺得這部書對他們具有威脅與傾覆的危險。我認為這部書由於它在史學素養上的廣度,在道德感上的深度以及表達方式上的雄渾有力,可說是儒家政治思想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職是之故,黃宗羲的著作在這些方面幾乎自成一格,但我們卻也不可以認為此書完全特異而與眾不同。黃宗羲並不是一個切斷他的過去、與他那個時代的學術格格不入的孤立的天才人物。相反的,黃宗羲的抗議只是把他同時代其他思想家的政治觀點作比較明確的表達而已。他這篇激越的宣言雖然因為朝代板蕩與外人入侵的危機而為之深刻化,但這篇文字不過是新儒家的自由傳統發展中一個高潮罷了。這個傳統是黃宗羲樂於認知並重新加以肯定的。
第一講 人之更新與道統 一般的新儒家思想,尤其是「道學」,是在北宋(960-1127)的偉大改革運動中興起的。在政治上,這些改革運動在王安石(1021-1086)決心推行「新法」(或新制、新政)的努力中達到了高潮。但是,此處的關鍵是「新」這個字,因為「新」似乎與宋代那種顯著的復古主義理想所表現的傳統相扞格,也就是説與那種認為應恢復古周制,於十一世紀的宋代實行的想法相衝突。但是事實上,這裏所表現的是因襲與革新齊頭並進,而非背道而馳。王安石之所以援引儒家經典,特別是《周官》來作為他激進改革的理論基礎,是因為這種形態的傳統提供了他攻擊現存制度的有力理由,而不是因為他的新制與《周官》書中相傳的典範有任何近似之處。 王安石感到必須替《周官》寫一本新的注解,並稱之為《周官新義》。這個書名頗有啟示性,正證明了當時人是努力於將傳統拿來作創新的運用。對經典的再詮釋援引了新的批評方法,以新的經學主張來為改革的目標效勞。因此,「復古」的主張恢復了,而三代的「聖王之道」也在實踐中變成新的可行之道。 王安石在追求他的目標時,雖因其所採用的權威式的做法與獨斷的態度而為人詬病,但是王安石深信從古制中可以尋獲新制的基礎,這一點在他同時代的大儒中則並非特例。例如哲學家程頤便曾用近似詹森總統(Lyndon Johnson)的「大社會」(Great Society)的詞彙,説在他們那個時代,需要大改革以興「大制」或「大利」,1其語氣之堅定稍不遑王安石。程頤在政治上舆王安石水火不容,但在引經據典以證明自己思想所具有的權威性這一點上,他與王安石一樣地獨斷。這種情形對王安石和程頤而言,都是很可能發生的,因為他們都認為「道」並非僵死於過去,反而對人類新的境遇兼具生命力與適應性。 宋代儒學中鼓舞這種想法的一個支派,就是對《易經》的研究。《易經》的繋辭傳特別強調「道」具有生生不已的活力與創造性。對道學早期的大師程頤而言,這個觀念正好與佛教以「變」為無常、以「道」為了脱生死輪迴的看法構成對比。《易經》書中所呈現的儒家形上學對於道提供了一個正面的看法,認為「道」永遠可為人類所理解,也永遠能適應一般人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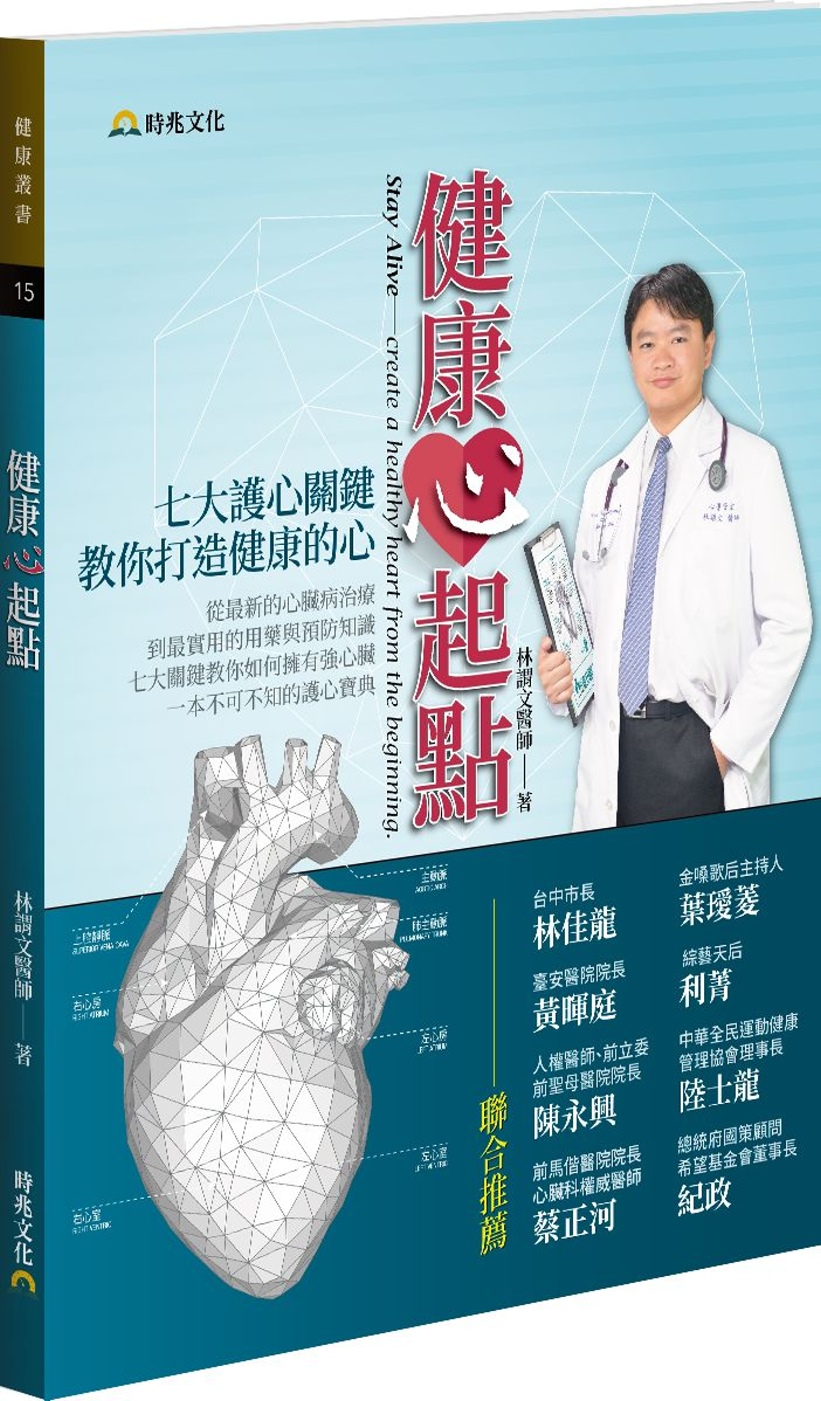 健康「心」起點:七大護心關鍵,教你...
健康「心」起點:七大護心關鍵,教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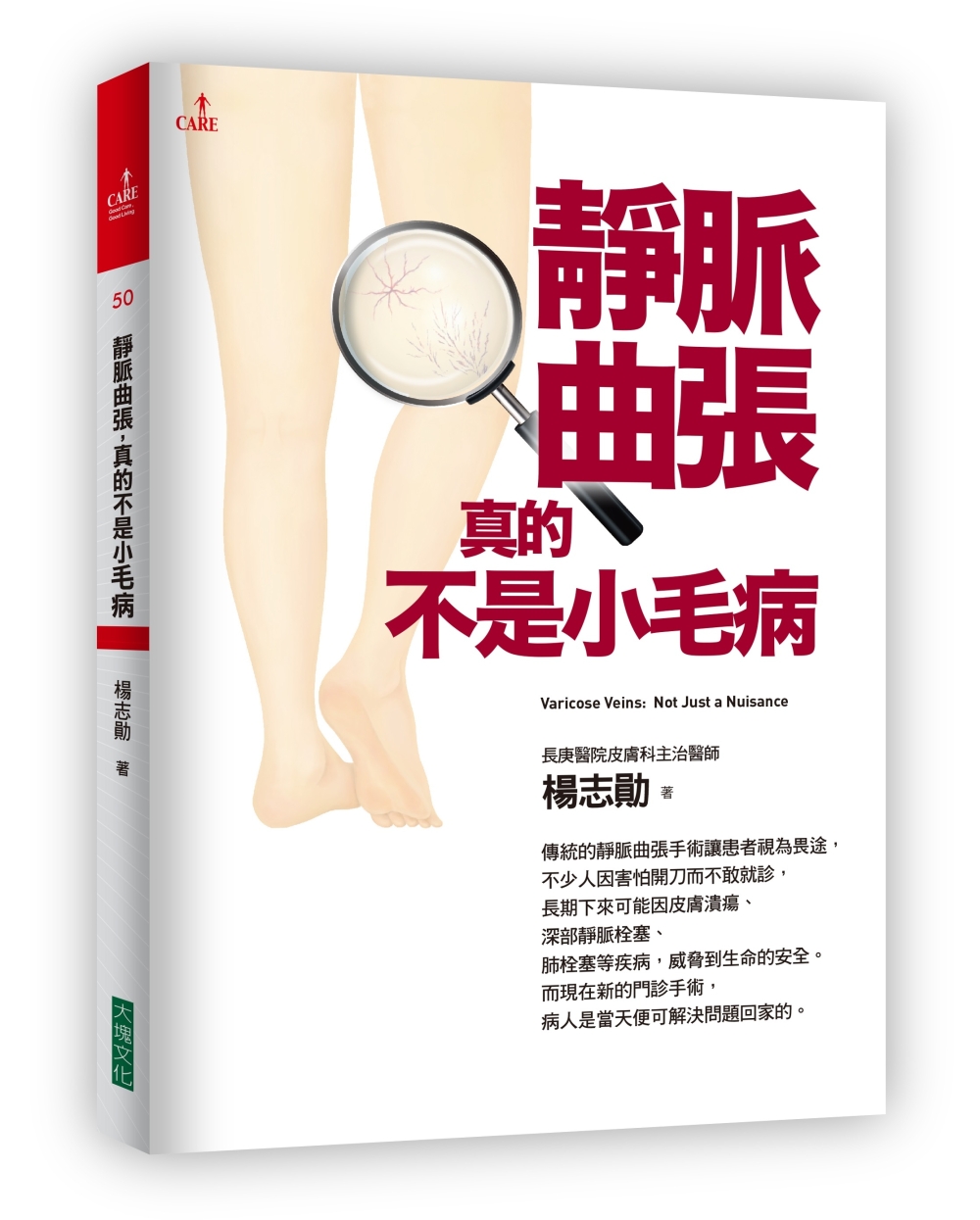 靜脈曲張,真的不是小毛病
靜脈曲張,真的不是小毛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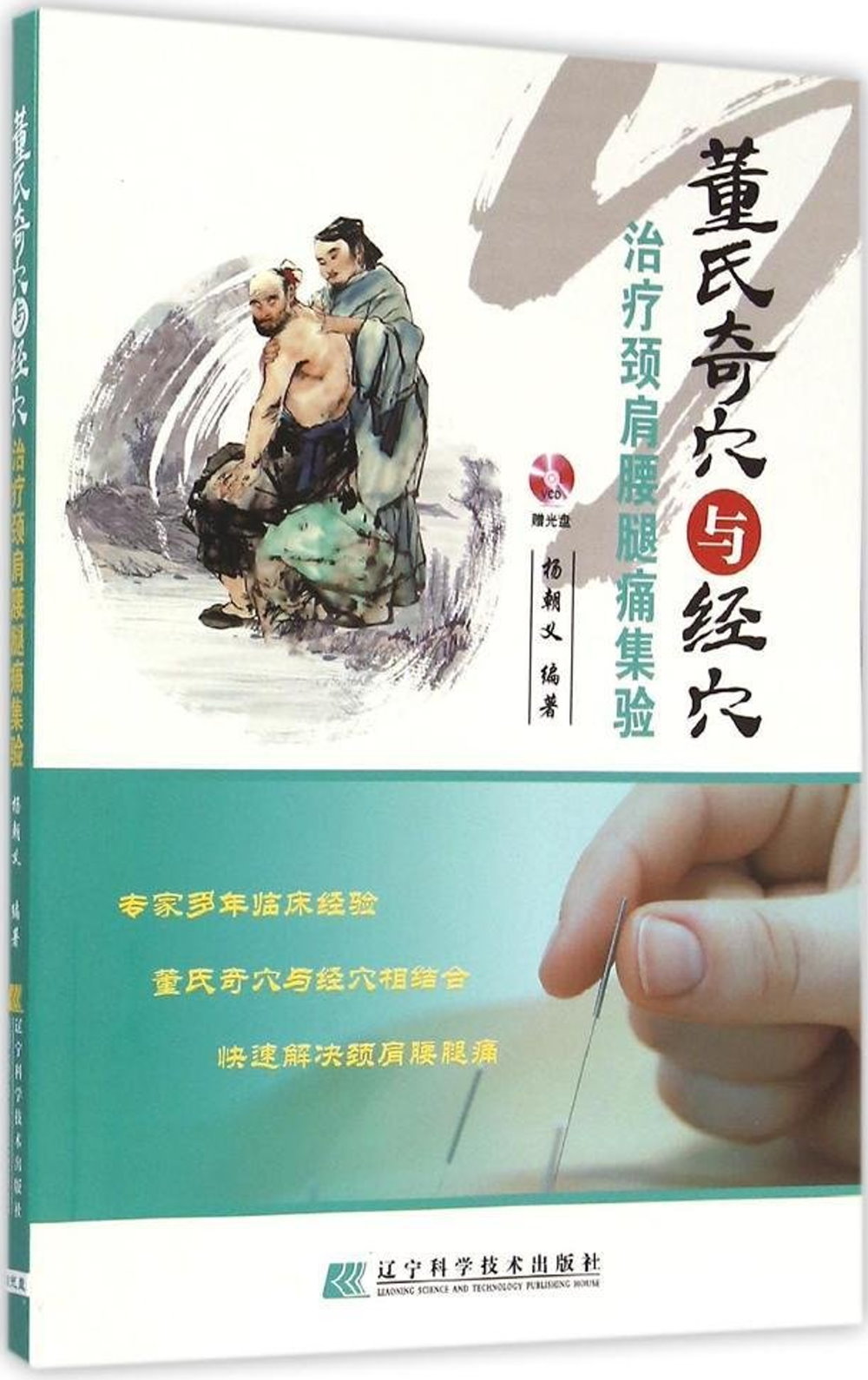 董氏奇穴與經穴治療頸肩腰腿痛集驗
董氏奇穴與經穴治療頸肩腰腿痛集驗 抓出全家人的毛病.家庭醫師guide
抓出全家人的毛病.家庭醫師guide 骨盆回正:療癒身心的練習帖
骨盆回正:療癒身心的練習帖 你又胃食道逆流了嗎?:「譚八點」解...
你又胃食道逆流了嗎?:「譚八點」解... 血流能解決所有煩惱:日本最熱門的健...
血流能解決所有煩惱:日本最熱門的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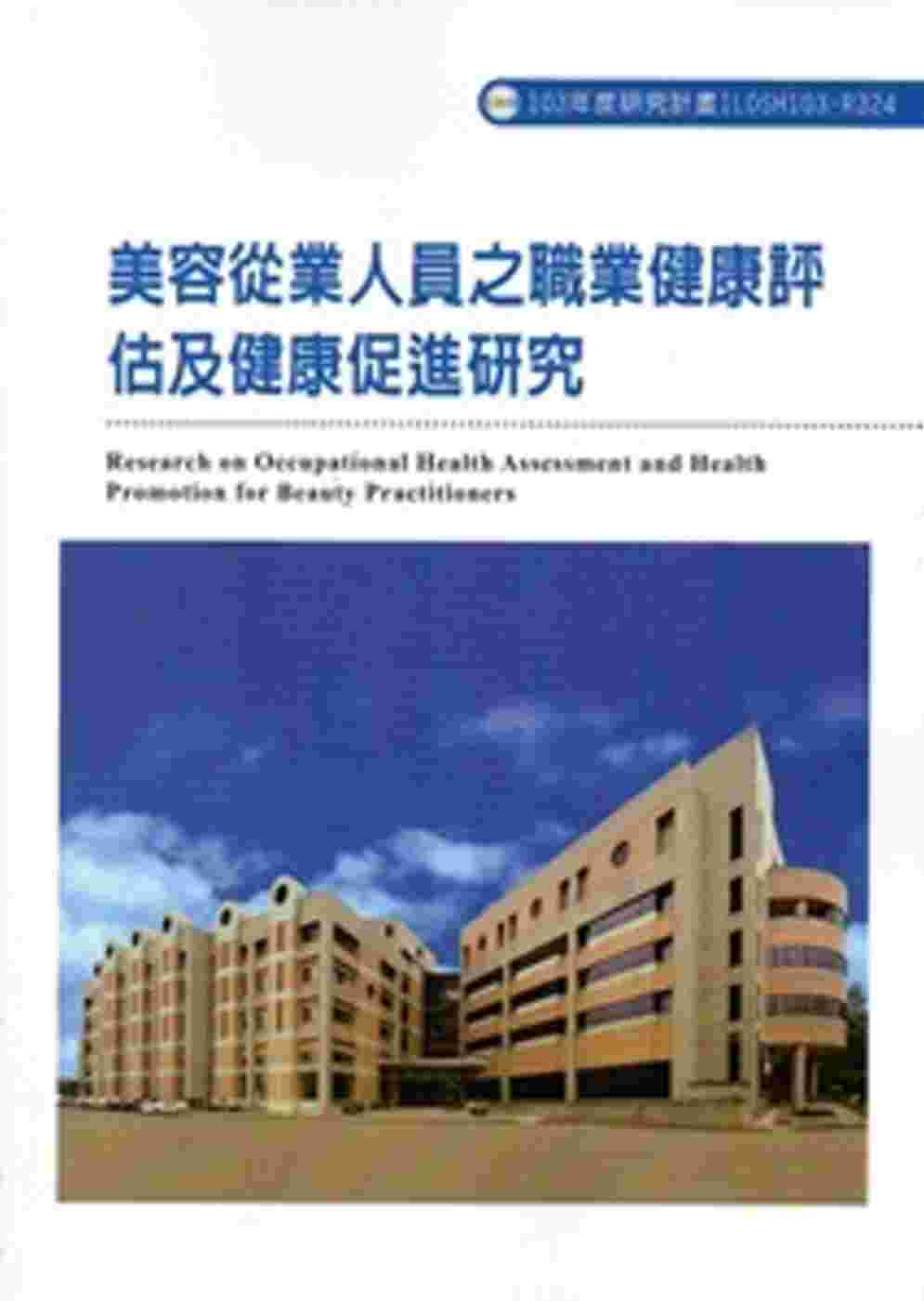 美容從業人員之職業健康評估及健康促...
美容從業人員之職業健康評估及健康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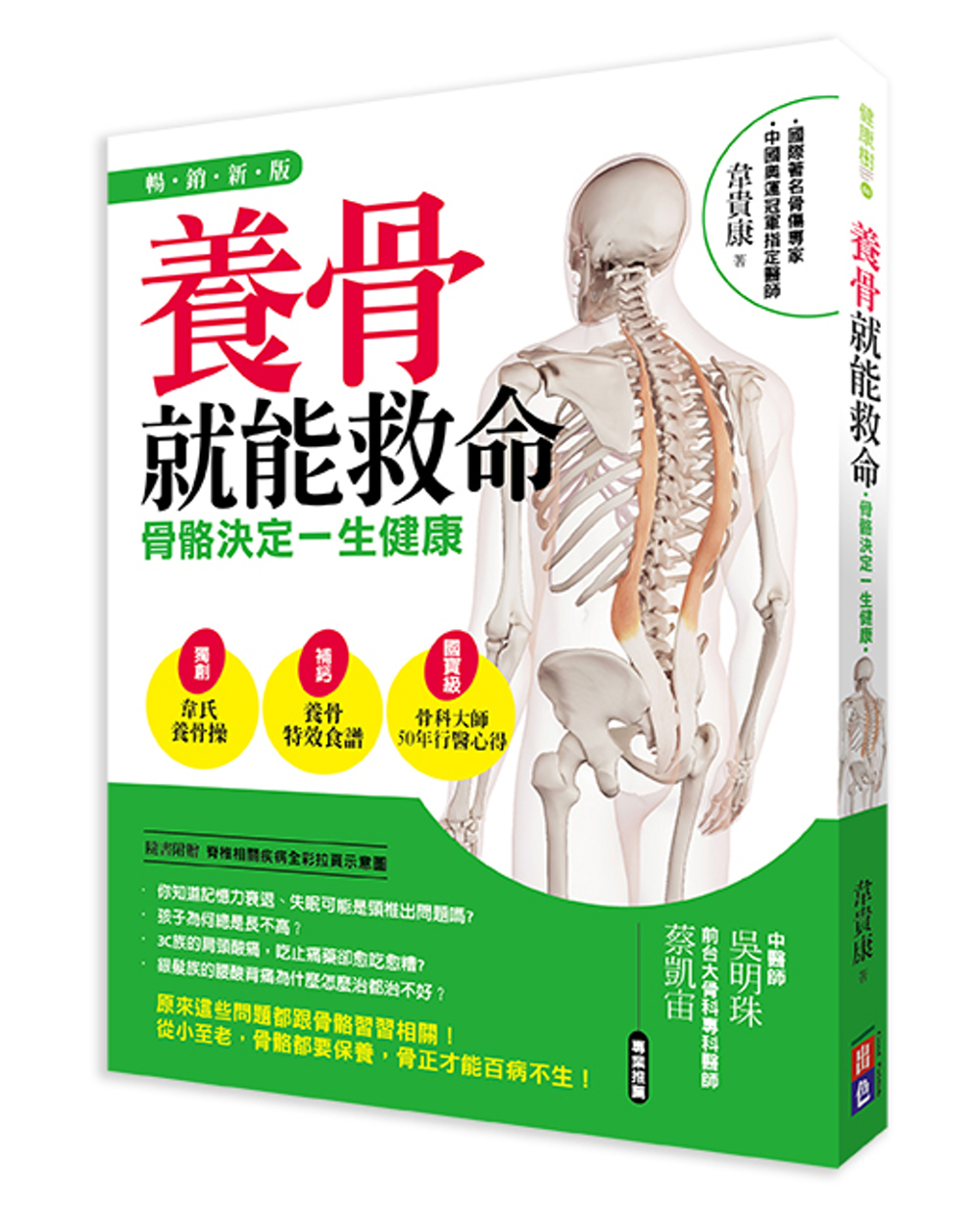 養骨就能救命:骨骼決定一生健康
養骨就能救命:骨骼決定一生健康 美肌女王
美肌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