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提琴家的大拇指:基因密碼裡關於愛情、戰爭與天才的失落傳奇 | 生病了怎麼辦 - 2024年5月

小提琴家的大拇指:基因密碼裡關於愛情、戰爭與天才的失落傳奇
DNA雙螺旋結構.發現六十週年紀念
人類真的差點絕種?遺傳學真能解釋愛貓女士對貓科動物的癡迷?DNA如何讓有些人天生沒有指紋?並讓另一些人長尾巴?基因是怎麼解釋美國甘迺迪總統那不完全來自曬太陽的古銅膚色,以及愛因斯坦的卓絕天才?是什麼樣的基因組合,造就出史上獨一無二的小提琴家帕格尼尼那超有彈性的大拇指和手指?DNA與基因(gene)這兩個概念現在大家雖然耳熟能詳,但早在十九世紀,它們其實是由不同人所發現的,而且沒有人知道它們是彼此相關的。光是生物學家如何研究DNA與基因,最後將兩者聯想在一起,再加上染色體,以及六十年前人類首度發現的DNA雙螺旋結構,最後發展出遺傳學,本身歷程就如同史詩一般精彩。本書將科學、歷史與文化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為我們釐清基因密碼的祕密,闡釋遺傳學如何為人類的歷史增添色彩,以及DNA將如何決定人類的未來。
一枚細胞裡的DNA足以伸展到近兩公尺長,而我們身體內的DNA,長度更是足以伸展到月球。在這些千纏百繞的雙股螺旋中,潛藏著許多歷史懸案的解答,而這些懸案,原本都是人們以為永遠無解的。
不過,人類幫基因解碼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遺傳學領域打從一開始,便充斥著大混戰、暗箭傷人,以及具有爭議性的理論——但是,科學家現在終於能夠判讀刻印在我們DNA中的奇妙故事,數百萬年前發生的老故事,其中包括人類如何在遠古時代勉強設法征服地球,甚至差點滅絕,絲毫看不出如現在人類所自我感覺良好的基因優勢。
隨著我們在繪製DNA地圖以及修改DNA方面,迭有進展,我們知道得愈多,改變DNA這件事,就愈顯得誘人,甚至令人渴望。DNA賦予我們想像力,而我們現在能夠想像,如何擺脫掉它加在我們身上,長達一輩子的手銬腳鐐。遺傳學今後也將繼續盤踞在科學界最熱門科目的寶座上,塑造出我們的身體結構,以及你我周遭未來的世界。
作者簡介
山姆.肯恩 Sam Kean
《紐約時報》暢銷書《消失的湯匙》(The Disapppearing Spoon)作者。他以優異的物理與英文科成績畢業於明尼蘇達大學。曾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修習寫作課程,並取得美國天主教大學圖書館科學的碩士學位。他也曾花了四年時間教授大學生與高中生,讓他對如何向大眾解析科學觀念更顯駕輕就熟。他的作品散見《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心理牙線》雜誌(Mental Floss)、Slate線上雜誌、《史密斯航太雜誌》(Space/Smithsonian)以及《新科學人》(New Scientist)雜誌。2005年取得美國科學促進會院士(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 Fellow) 榮銜。也是DCWA科學寫作協會會員(DC Science Writer’s Association)。2009年,榮獲美國科學作家協會頒給三十歲以下最佳科學作家的Evert Clark/Seth Payne獎座第二名。並獲選為2009-2010年度的「米德柏利環境報導研究員」(Middlebury Environmental Journalism Fellow)。
譯者簡介
楊玉齡
輔仁大學生物系畢業。曾任《牛頓》雜誌副總編輯、《天下》雜誌資深文稿編輯,現專任自由翻譯寫作,以科普書籍為主。著作《肝炎聖戰》(與羅時成合著)榮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創作首獎金籤獎、《台灣蛇毒傳奇》(與羅時成合著)榮獲行政院新聞局第二屆小太陽獎;譯作《生物圈的未來》榮獲第二屆吳大猷科普譯作首獎金籤獎、《消失的湯匙》榮獲第六屆吳大猷科普譯作銀籤獎、《大自然的獵人》榮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譯作推薦獎、《雁鵝與勞倫茲》榮獲中國大陸第四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三等獎。
前言
PART IA,C,G,T,以及你如何閱讀基因的樂譜?
1基因,怪物,DNA生物怎樣把特徵傳給下一代?
2達爾文差點陣亡遺傳學家為何想殺掉天擇?
3 DNA就這樣壞掉了大自然如何閱讀——以及錯讀——DNA?
4 DNA樂譜DNA儲存了什麼樣的資訊?
PART II 我們的動物身世製造爬跳、嬉戲與殺戮
5 DNA的辯解生物為何演化得這麼慢——但複雜度卻又大爆發?
6生還者,肝臟人體最古老、最重要的DNA是誰?
7馬基維利微生物在人類DNA裡,有多少真正屬於人類?
8愛情與返祖現象哪些基因讓哺乳動物成為哺乳動物?
9人猩,以及險些釀成的災難人類何時與猴子分手,為什麼?
PART III基因與天才人類如何變得如此人類?
10 猩紅字A’s,C’s,G’s與T’s為何人類幾乎絕種?
11 尺寸很重要人類怎麼會長出這麼大顆的腦袋?
12基因的藝術我們的DNA有多深的藝術天分?
PART IV DNA先知遺傳學對歷史、現在和未來的影響
13 有時候,歷史就是序文對於史上英雄人物,基因能(或不能)告訴我們什麼?
14三十億個小碎片為什麼人類的基因數不比其他物種多?
15 來得快,去得快?同卵雙胞胎為何不完全相同?
16我們熟知(以及不知)的生命接下來,要怎麼辦?
後記
致謝
註釋
參考書目
前言
我想咱們還是先打開天窗說亮話。這本書講的是DNA—講的是如何把埋藏在我們DNA裡長達數千、乃至數百萬年的許多故事,挖掘出來,以及如何利用DNA來解開一度被認定無解的人類之謎。沒錯,我在寫這本書,雖然我父親的名字就叫做「基因」(Gene),我母親的名字發音也一樣(Jean),所以他們是Gene和Jean賢伉儷。全名念起來是Gene and Jean Kean。除了發音好像念經一樣怪之外,我爸媽的名字也把我害慘了,讓我從小飽受嘲弄:我的錯誤,我的缺點,總是被追溯到「我的基因」,我要是不小心做了什麼蠢事,旁人就要揶揄道「都是我的基因的錯」。至於我父母必須經由性行為,才能把基因傳給我這件事實,更是火上加油,只會讓那些嘲弄加倍尖酸,完全沒法回嘴。
結果,從小一碰到科學課在教DNA和基因,我就害怕,因為我知道,只要老師一轉身,不出兩秒鐘,就會有人消遣我了。就算沒有人真的說出口,也一定有人在腦袋裡想那些笑話。即便(或說尤其是)在我開始了解DNA多麼強大有力之後,那種巴夫洛夫制約式的緊張,還是如影隨形地纏著我。上高中後,我終於不在乎嘲笑了,但是基因這個字眼,依然會令我產生許多即時的反應,有些還算愉快,有些則不。
但在另一方面,DNA也令我興奮。科學界再沒有一個主題比遺傳學更大膽,再沒有一個領域有希望將科學推進到這般地步。而且,我指的也不限於一般的(往往過度誇大的)醫療遠景。DNA為生物學的每個領域注入新的生命力,同時也改造了有關人類的研究。但在此同時,每當有人開始深究我們的基本生物性,我們卻又不免抗拒—我們不願意被貶低為只不過是一堆DNA。而且,一聽到有人討論要怎樣修補這些基本的生物性,我們更是膽戰心驚。
更曖昧的是,DNA提供了一個強力的工具,來挖掘我們的過去:生物學藉由某些途徑,搖身一變成了歷史學。在過去幾十年間,遺傳學家便已經揭露了如聖經般有價值的精彩故事,它們的情節原本被認為早已不可考—要不是年代太過久遠,就是殘留的化石或人類學證據太少,無法拼湊出完整的故事。誰知道,後來發現,原來我們一直把那些故事帶在身上,長久以來,我們細胞裡那些小小修道士,在DNA的黑暗時代,無時無刻,分分秒秒,忠實記錄下來的數兆個文字,一直在等待我們去破解這種語言。這些故事包括一些宏觀的偉大傳說,像是我們打哪兒來,以及我們如何從一堆爛泥演化成地球上已知最具主宰力的生物。但是,這些故事也會以極為個人化的方式,進駐到家庭裡面。
要是我的學校生活能有一次重來的機會(除了幫爸媽編一個比較安全的假名之外),我會在樂隊裡選擇不一樣的樂器。那倒不是因為我是四、五、六、七、八及九年級生當中,唯一的男生豎笛手(至少不完全是這個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我在控制豎笛上那些個氣孔和連桿時,老是笨手笨腳的。而且這和缺乏練習一點關係都沒有。我責怪的對象是我那異常彎曲的手指,以及伸展開來會往後彎的大拇指。在吹豎笛時,我得把手指摺成一堆笨拙的結,弄得我老是覺得需要壓一壓那些關節,而且它們還會隱隱作痛。偶爾,我的大拇指甚至會卡住,動彈不得,還得動用另一隻手去把它的關節扳開。我的手指就是不如那些技法高妙的女生豎笛手。我告訴自己,這些毛病都是天生的,是我從爸媽的基因庫裡遺傳到的。
離開樂隊後,我自然沒有理由再去深思手部靈巧與音樂能力的推論,直到十年後,我得知小提琴家帕格尼尼(Niccolo Paganini)的故事。此人的才華是這麼地高妙,害他一輩子都在闢謠,否認曾經與撒旦簽約,用靈魂換取才華(他故鄉的教堂在他死後幾十年,依然拒絕埋葬他)。事實證明,帕格尼尼簽約的對象,是一位更精緻巧妙的大師:他的DNA。幾乎可以肯定,帕格尼尼天生具有某種遺傳毛病,讓他擁有超級彈性的手指。由於他的結締組織實在太有彈性,他可以把小指頭伸展到與其他指頭成直角的程度(你可以試試看)。而且他的手掌展開的寬度,也異於常人,這些構造對於拉小提琴來說,都是一大優勢。我那簡單的假設—有些人天生就能(或是不能)演奏某種樂器,看來確實很有道理。照理說,我可以放下這個議題了。然而,我繼續探究,結果發現帕格尼尼的症狀很可能也造成嚴重的健康問題,像是關節痛,視力差,呼吸衰弱,以及令他終生苦惱的疲憊。對於一大早爬起來練習軍樂隊,弄得手指關節僵硬,我也有滿腹牢騷,然而帕格尼尼卻得經常在職業生涯的高峰期間,取消演奏會,他在過世前幾年甚至無法再公開演奏。就帕格尼尼來說,對音樂的熱情,配上正好合用的身體缺陷,世間恐怕再沒有比這個更好運的了。然而,這些缺陷也加速了他的死亡。帕格尼尼可能不是自願要簽訂他那套基因合約,但是他身不由己,就像我們所有人一樣,而他的那套基因合約,既造就了他,也毀滅了他。
但是還沒完,DNA要告訴我的故事還多著呢。有些科學家回溯歷史,逆向診斷出達爾文、林肯甚至埃及法老王曾經罹患的遺傳疾病。另外一些科學家則直接探索DNA,以便清楚地說出它最深奧的語言特性,以及令人驚喜的數學美感。事實上,高中期間,當我還在樂隊、歷史、數學以及社會等課堂間穿梭之際,DNA的故事便不斷地從各種文獻裡冒出來,將各種不同的主題串連在一起。DNA訴說了核爆倖存者的故事,也訴說了探險家在北極早夭的故事。關於人類幾乎滅絕的故事,或是懷孕的母親將癌症傳給新生兒的故事。其中有些故事,就像帕格尼尼,是科學闡明了藝術,但是另外一些故事,例如科學家透過畫像來追溯基因缺陷,則是藝術闡明了科學。
還有一件事實,雖然我們早就在生物課上學到,但剛開始卻不懂得讚美,那就是DNA分子的長度。雖說DNA被包裹在已經夠小的細胞裡的一個小櫃子裡,但是它們一旦展開,卻可以延伸得非常遠。某些植物細胞裡的DNA足以伸展到三百英尺長;一個人體內的DNA能伸展的長度,大約足夠從冥王星到太陽往返一趟;地球上所有DNA集合起來的長度,足以橫越目前已知的宇宙許許多多趟。而我愈是探究DNA的故事,愈是把這種不斷延伸的性質—不斷地解開纏繞,愈走愈遠,甚至還能往回溯及歷史—視為DNA的本質。所有人類活動都在我們的DNA裡留下鑑識痕跡,而且不論DNA記錄的故事是關於音樂,運動,還是狡猾的馬基維利微生物(Machiavellian microbe),這些故事加總起來,敘述的是一則更大、也更複雜的人類傳奇,人類在地球崛起的經過:為何我們會成為地球上最荒謬的動物之一,但同時又是萬物之靈。
不過,在我的興奮之情底下,基因還有它令我惶恐不安的另一面。在研究撰寫本書期間,我把我的DNA交付給一家基因檢驗公司,雖說價格不便宜(四百一十四美元),我還是很隨性地就做了。我知道,現階段個人的基因檢驗還有很嚴重的缺點,就算科學上沒問題,但結果通常也沒有多大幫助。我可能會從我的DNA檢驗中得知,我有綠色的眼睛,但是,我只要照照鏡子,一樣可以知道。我也可能得知,我的身體不太擅長代謝咖啡因,但是,我早就有過無數個晚上喝可樂便睡不好的夜晚。再說,DNA採樣過程也實在讓人很難把它當一回事。我收到一份郵件,裡頭有一個小塑膠瓶,它的蓋子好像橙色的玉米糖,附加一份說明書,叫我用指節按摩我的臉頰,讓口中的一些細胞脫落。然後,我要不斷地朝小瓶子吐口水,直到裝滿三分之二瓶。單單這個動作,就耗掉我十分鐘,因為說明書上很嚴肅地指出,不是隨便什麼口水都可以。必須是上好的、黏稠的、像糖漿一樣的口水;就像一口啤酒,不應該有太多泡沫。第二天,我把這個小痰盂寄出去,然後就準備迎接列祖列宗給我的小驚喜。我並沒有深思這整件事,直到上網註冊我的檢驗,讀到一份說明,有關篩檢太過敏感或是可怕的資訊。檢驗單位表示,如果你的家族有乳癌或阿茲海默症或其他疾病—或者你雖然沒有家族病史,但卻害怕知道它們的消息—他們可以提供阻擋該項資訊的服務。你可以圈選某些空格,讓特定項目保持機密,不讓任何人,包括你自己,得知該項檢驗的結果。真正嚇到我的,是帕金森氏症的空格。在我有記憶以來,最早期的記憶之一,同時也是最糟糕的記憶,就是有一次我在祖母家的走廊上閒逛,碰巧把頭探進祖父的房間,罹患帕金森氏症的他,一直躺在那個房間裡,直到去世。
我父親在成長過程中,不斷聽到旁人說他長得有多像我祖父—而我也聽到類似的看法,說我長得多麼像我老爸。於是,當我不小心晃進那個房間,看到一名白髮版的老爸倚在有鐵欄杆圍繞的床上時,我彷彿看到了我自己。我記到屋裡有好多白色的東西—白牆,白地毯,白床單,以及他身上那件背後開襟的罩袍。我記得他身子往前傾,幾乎快要翻倒,罩袍鬆開了,一撮白髮垂了下來。
我不確定他有沒有看到我,但是就在我猶豫地站在門檻上時,他突然開始呻吟和顫抖,聲音也跟著哆嗦起來。就某方面來說,我祖父算是幸運的;我祖母是護士,可以在家就近照顧他,而且他的幾個孩子也會固定來探視。但是他的心理與生理都已經退化了。我還記得那些濃濃的、彷彿糖漿似的唾液,垂掛在下巴上,那裡頭,想必充滿了DNA。那年我大約五歲,還太小,不懂事。直到現在,我想起來還覺得慚愧,當時我竟然轉身跑掉了。
如今,陌生人—更糟的是,還有我自己—都能偷看到我的DNA,看看那個可能引發我祖父罹患帕金森氏症的自我複製分子,是否也窩藏在我的細胞裡。很有可能是沒有。我祖父的基因在父親體內,已經被祖母的基因稀釋了一半,然後我父親的基因在我體內,又被我母親的基因稀釋了一半。但機率當然還是存在。我不怕面對罹患各種癌症或是其他的退化性疾病的可能性。但是對於帕金森氏症,我辦不到。於是,我把那個空格塗滿了。
像這樣的個人切身故事,同樣屬於遺傳學的一部分,不輸其他偉大刺激的歷史故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我們每個人體內,至少都埋藏了其中一個故事。這也是為什麼,本書除了講述那些歷史故事之外,同時也會把那些故事建構起來,並將它們與各種DNA研究連結在一起,不論是已經完成的研究,還是未來可能完成的。這些遺傳學研究以及它們將會帶來的改變,好比移動的洋流,巨大而且無法避免。但是,當它的影響力最後抵達我們所在的岸邊時,將不會像一場海嘯,而比較像一群碎浪。當潮水拍打上岸時,不管我們覺得要站得離水岸多遠才能頂得住,我們感受到的,將會是個別的波浪,一波接著一波。
但還是一樣,我們可以防患於未然。就像某些科學家所體認到的,DNA故事已經真正取代了舊日學院裡的西洋文明課程,成為人類存在的偉大故事。了解DNA,有助於我們了解自己來自何方,以及我們的身心如何運作,此外,了解DNA的限制,也有助於我們了解自己的身心為何無法運作。此外,同樣程度地,我們也必須做好準備,聆聽DNA所說(以及沒有說)的一些棘手的社會問題,像是性別、種族的關係,或是某些特性(例如攻擊與智慧)究竟是不是註定的,還是可以改變的。另外,雖然我們承認還不完全了解DNA的運作方式,但仍舊必須決定,是否要信任那些熱心的思想家,他們已經在大談人類有機會(甚至有義務)去改進四十億年來的生物學。對於這種觀點,最了不起的DNA故事便是:我們的種族已經存活得夠久遠,(有可能)可以操控自己了。
本書所講述的歷史,還在建構之中,而我為《小提琴家的大拇指》設計的架構是,每一章只回答一個問題。我這堆包羅萬象的故事,從微生物的久遠歷史開場,接著推進到我們的動物祖先,在靈長類和原始人競爭者(例如尼安德塔人)身上稍事停留,然後在「文明的現代人,帶著華麗的詞藻與碩大的腦袋登場」之際,達到最高潮。然而,當本書來到最後一部時,所探討的問題卻還沒有完全解答。有些事還不確定,尤其是下面這個問題:這場不惜撼動一切根本,以求了解我們的DNA的偉大人類實驗,最後將如何收場。
6生還者,肝臟人體最古老、最重要的DNA是誰?長久以來,所有小學生都知道,在殖民盛行年代,歐洲商人與王室曾經浪費不知多少銀兩,來搜尋西北航道(Northwest Passage)—一條能橫切過北美洲的航線,讓歐洲直通盛產香料、瓷器與茶葉的印尼、印度和中國。然而,比較不為人所知的是,早期探險家其實也花了同樣多的心血和妄念,去搜尋一條能繞過天寒地凍的俄羅斯北方的東北航道。其中一位搜尋東北航道的探險家巴倫支(Willem Barentsz),來自荷蘭沿海低地,是航海家兼地圖繪製師,英文典籍中的Barents、Barentz、Barentson和Barentzoon,都是指他。一五九四年,巴倫支第一次出海尋找該航道,進入現今挪威北方的巴倫支海(Barents Sea)。巴倫支所進行的這類型航海,雖然是基於商業目的,但是也造福了科學家。博物學家雖然會擔憂傳言中偶爾會出現的荒島怪獸,但如今總算可以開始描繪植物相與動物相在世界各地有何差異—這些研究,可以說是「現代探討共通祖先、共通DNA」的生物學的先驅研究。地理學家也因此獲得急需的協助。當時很多地理學家都相信,由於高緯度地區的夏季整天都有陽光,到某個時候,極地的冰帽會融解,讓北極成為一個陽光普照的樂園。而且幾乎所有地圖都把北極畫成一大塊黑色的磁石,因為這樣一來,就能解釋為何它這麼會吸引羅盤。在動身前,巴倫支的目標是想弄清楚,位於西伯利亞北邊的新地島(Novaya Zemlya),究竟是另一塊尚未發現的大陸的一個岬角,或者只是一個可以繞行的島嶼。他總共得到三艘船的裝備,分別是水星號(Mercury)、天鵝號(Swan)以及另一艘水星號,並且在一五九四年六月啟航。幾個月後,巴倫支帶著他的水星號組員與其他兩艘船分開,開始探索新地島的海岸。此舉堪稱探險史上非常大膽的行動。水星號一連好幾週,都在忙著閃躲一支由浮冰組成的西班牙無敵艦隊,長達一千五百英里。最後,巴倫支的手下疲憊不堪,懇求返航。既然已經證明他能航到北極海,巴倫支大發慈悲,掉頭回到荷蘭,心裡認定自己發現了一條比較容易通往亞洲的航道。是啊,比較容易,只要他能避開怪獸。新世界的發現,以及非洲與亞洲地區的持續探險,導致大量歐洲人連做夢都難以想像的動物與植物,不斷地出現—同時,也激發出同樣怪誕的野獸傳說,是水手們信誓旦旦親眼見到的。至於繪圖師,更是充分發揮了內在的驚悚畫家天分,為空白的大海加油添醋,在他們的地圖上安插了狂野的場景:血紅色的大海怪把船擊碎,巨大的海獺彼此吞噬,龍貪婪地咀嚼老鼠,樹木用鎚矛般的樹枝敲打熊的腦袋,更別提永遠上空的美人魚。有一張很重要的航海圖,繪製於一五四四年,上面就畫了一個沉思中的獨眼巨人,坐在非洲西邊的彎鉤上。這張圖的繪圖師是明斯特(Sebastian Münster),他後來發表了一本很具影響力的地圖集,裡面穿插了各種怪獸的短文,介紹半獅半鷲(griffin),以及忙著挖金礦的貪婪的螞蟻。而且明斯特還滔滔不絕地大談世界上各種長得像人類的怪物,包括臉長在胸部的無頭族(Blemmyae);長著狗臉的犬頭人(Cynocephali);以及一種叫做遮陽腳(Sciopods)的醜怪的陸上人魚,它們僅有一隻大腳,每每在烈日當空時,躺下身,把大腳高舉過頭部,用來遮陽。這些怪獸,有些只是將古老的恐懼或迷信加以擬人化(或是擬動物化)。但是其中也混雜了一些貌似真實的神話以及奇妙的事實,博物學家幾乎趕不上他們。在那個探險的年代,即便是最富科學精神的博物學家林奈(Carl von Linnĕ,也就是Carl Linnaeus),都會思考這些怪獸。他的大作《自然系統》(Systema Naturae)建立了我們至今仍在使用的二名法,來幫物種命名,所以我們現在也才有諸如Homo sapiens(智人)與Tyrannosaurus rex(暴龍)這樣的學名。同時,林奈這本書還把一類動物歸入「奇異動物」(paradoxa),包括龍,鳳凰,森林之神薩特,獨角獸,由樹上嫩芽變成的鵝,海克力士的天敵多頭蛇,以及不只會隨著年齡愈變愈小,而且最後會變成魚的奇特蝌蚪。現在看到這些,我們可能會大笑,但是其中至少有一個例子,可笑的是我們:愈長愈小的蝌蚪確實存在,只不過這種叫做奇異多趾節蟾(Pseudis paradoxa)的蝌蚪,最後會縮小成尋常的老青蛙,而非變成魚。不只如此,現代基因研究還發現,林奈與明斯特的傳奇故事,是有一項根據的。在每個胚胎中,都有幾個關鍵基因扮演其他基因的繪圖師角色,利用全球定位系統那樣的精準度,來繪製身體地圖,從前到後,從左到右,以及從上到下。昆蟲、魚類、哺乳類、爬蟲類以及所有其他動物,都共用許多這類型基因,尤其是hox基因群(全名為homeobox genes,同源盒基因)。在動物王國裡,無所不在的hox基因解釋了,為何全世界的動物都擁有相同的基本身軀計畫:圓柱體身軀,一端是頭,另一端是肛門,中央地帶則長出各種不同的附屬肢體(單單根據這個原因,傳說中,臉孔位置低得可以舔自己肚臍的無頭族,就很不可能存在)。就基因來說,hox有一個很不尋常的地方,經過幾億年演化之後,它仍然緊密相連,幾乎總是一起出現在一段連續的DNA中(無脊椎動物這一段DNA大約有十個基因,脊椎動物有四段基本上相同的DNA)。更不尋常的是,每個hox基因在那段DNA上的位置,都與它管轄的身體部位相對應。譬如說,第一個hox基因設計頭頂。下一個hox基因設計稍微低一點的部位。第三個hox基因再稍微低一點,以此類推,直到最後一個hox基因,負責設計我們身體最下方的部位。為什麼大自然需要在hox基因裡,埋下一張從頭到腳的空間地圖,目前並不清楚,但還是一樣,所有動物都展現這個特性。
 犬之島 動畫電影製作特輯+電影改編...
犬之島 動畫電影製作特輯+電影改編... 清秀佳人(親子彩色圖文本)
清秀佳人(親子彩色圖文本) 公主殿下 美肌魔法時光:既是活潑繪...
公主殿下 美肌魔法時光:既是活潑繪... 灰王子
灰王子 孟孟的好好用安心皂方:加進生活食材...
孟孟的好好用安心皂方:加進生活食材... 那些不能告訴大人的事
那些不能告訴大人的事 「超級穀物」簡單料理提案:藜麥、燕...
「超級穀物」簡單料理提案:藜麥、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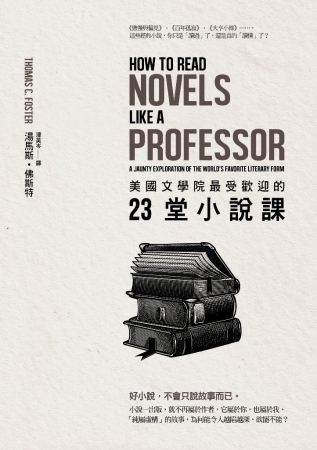 美國文學院最受歡迎的23堂小說課
美國文學院最受歡迎的23堂小說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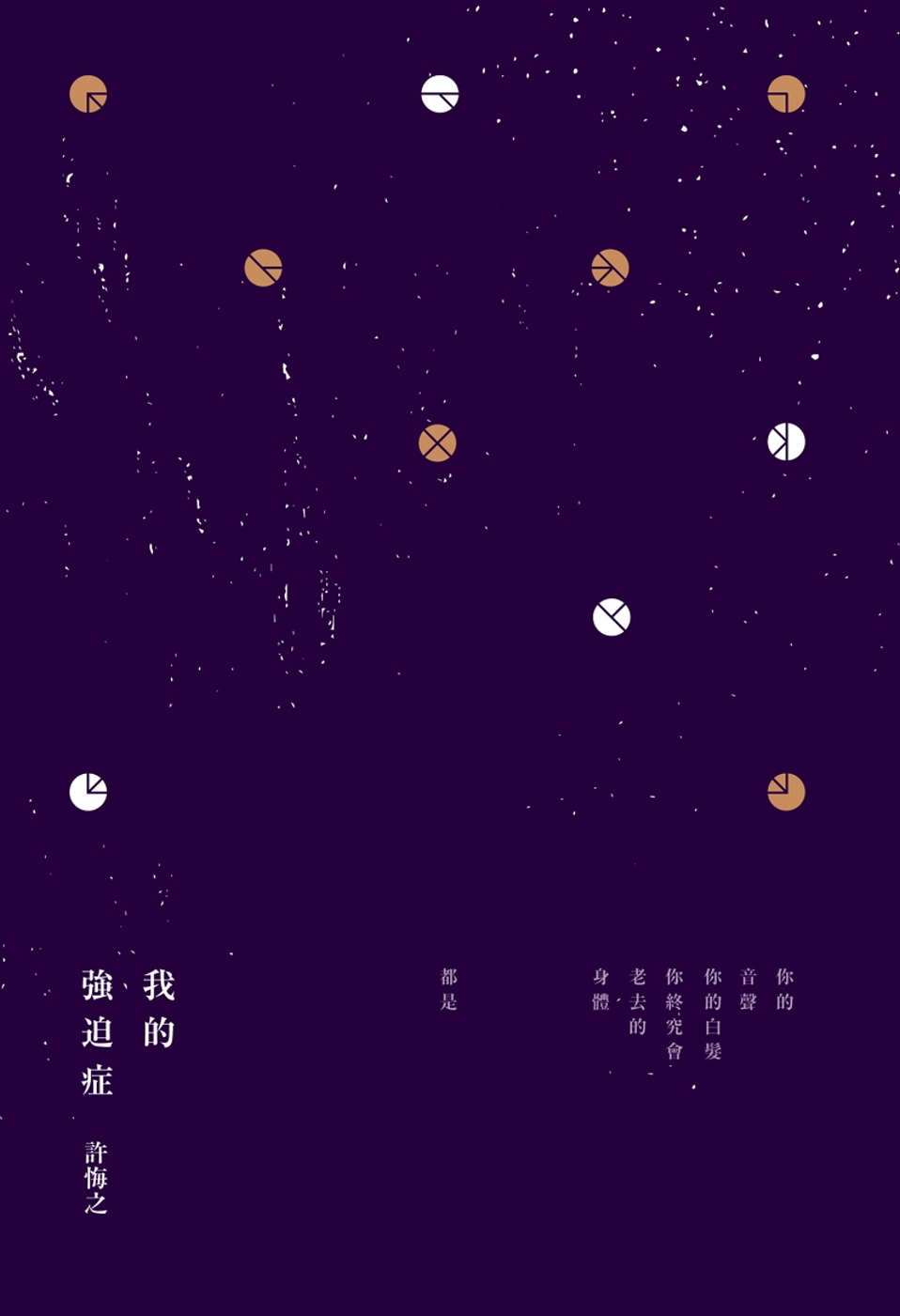 我的強迫症
我的強迫症 企鵝的憂鬱
企鵝的憂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