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悲懷(紀德逝世六十五週年紀念‧人生二部曲之二) | 生病了怎麼辦 - 2024年11月

遣悲懷(紀德逝世六十五週年紀念‧人生二部曲之二)
愛使人投身理想,予人自由的卻是欲望。
他勇於與時代對決,真理卻無法為他解答痛失摯愛之苦⋯⋯
他的意圖不是身處於當下,而是讓愛與真理溢出時間之外。
他的寫作不是為了同代人,而是為了下一個世代。
他明白今天的小眾,必將成為明日的輿論──
──當代的異端・後世的先驅者──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紀德劃時代經典作
◎跨越百年的精神典範啟發卡繆、沙特、德希達等名家的一代大師
◎收錄作家阮慶岳專文〈鞦韆上的假面天使〉深入導讀紀德最矛盾的懺情告解
◎收錄紀德日記選永恆的自我論戰──談藝術、詩、真理、政治、性別、宗教
◎法文直譯本首度在台問世「法語譯者協會翻譯獎」首屆獲獎譯者擔綱翻譯
◎經過刪改、再三編纂,直至紀德逝後才問世的完整版本
書寫妳的我、追悼妳的我、傷害妳的我、珍愛妳的我,
無論是哪一個我,
唯有和妳有關的那個我,才是我最精華的部分。
瑪德蓮,妳離去之後,我該怎麼相信永恆?
結縭四十載,紀德深愛的妻子瑪德蓮撒手人寰。瑪德蓮是他自小最珍惜的靈魂友伴,也是在他作品中占據最多篇幅的繆思女神。在她出現之前,他的世界只有一片混沌與黑暗。然而婚姻生活卻長年積累著懷疑、背叛,與日漸增長的沉默。他堅稱深愛妻子,那份愛高度貞潔,因不含肉欲成分而完整神聖;瑪德蓮則為了丈夫在外尋歡、陶醉於同性情欲而深感痛苦,日漸憔悴,心門緊閉。
在《如果麥子不死》的末尾,紀德彷彿將從婚姻中找到救贖,然而紀德逝後才出版的《遣悲懷》中,卻坦率揭露滿腔理想也無法治癒的傷痛。紀德在其中書寫的是無能傳達的愛、自我放逐式的裸裎懺悔,是最深的愛也是最令人懊喪的背叛,更是面對著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真理代言者,以獻祭之姿全心傾吐。
本書另收錄紀德親選的〈瑪德蓮日記〉,以及〈紀德日記選〉,時間從一八八九年橫跨至《如果麥子不死》出版後的一九二三年,作為「人生二部曲」之銜接。紀德對自身日記自道:「但願有朝一日,某個跟現在的我年齡相仿、價值觀雷同的年輕人在翻閱拙著時會感到悸動,感覺自己受到重塑。除此之外,我沒有其他野心。」他在日記中進行最嚴格的靈魂演練,深談時代的盲目、一次大戰前後的政治思潮、創作者的自省與窠臼、愛與情欲的忠實描摹、宗教與真理的交鋒辯證。彷彿操作著一場永不停歇的自我解剖,試圖還原愛與真理的原貌。
──有關「遣悲懷」書名──
●原文書名Et nunc manet in te典出古羅馬詩人魏吉爾詩歌作品,內容描述一名牧羊人在樹下午睡時,一條蛇朝他爬行,這時一隻小飛蟲忽然停在他的眼睛上,牧羊人醒來伸手將牠打死,同時驚見正準備咬他的蛇,於是及時把蛇殺死。牧羊人感念小飛蟲救命之恩,為其蓋了一座墓,小飛蟲「就此長存你心」(et nunc manet in te)。紀德援引此句為本書書名。
●一九七○年晨鐘出版的《遣悲懷》,係由聶華苓女士譯自一九五二年倫敦Secker&Warburg英文版,中文書名「遣悲懷」由周棄子所賜,典出元稹悼亡詩詩題。二○一六年版本沿用。
──名句摘錄──
●我不知道哪件事比較可怕:是不再被愛,還是看到我們愛著的、而且他也愛著你的那人不再相信你的愛?
●生活終究重新披上幸福的虛假外衣。
●回溯到最久遠的初始,我看到的只是她。除此之外,在我最稚嫩的歲月中,就只有一片闇黑,我只是在其中摸索前行。
●她的一滴眼淚都比我的幸福汪洋更深重。
●即便是靈魂最透明的人,也不會讓別人看見其中的許多折曲,就算是愛著自己的人也不例外。
●我寫作不是為了下一個世代的人,而是為了再下一個世代。
●很少有哪一天我不會對一切拋出質疑。
●創作任何新作品時,絕不可濫用寫前一部作品時獲得的衝勁。同理,必須為每一部新作品征服一批新的群眾。
●人不應該只要一個東西,而且不斷要它。我們確信這樣就可以得到它。但我呢,我什麼都想要;所以我什麼都得不到。我總發現——而且總是發現得太晚——某個東西降臨時,我正在追求另一種東西。
●就我本身而言,想像鮮少先於想法而來;令我激昂的是想法,絕不是想像;但倘若只有想法而沒有想像,那就還不會有任何東西產生;那是一股缺乏效能的灼熱。作品的想法,就是它的構成。
●當我不再憤慨時,那將代表我開始邁入老年期。
●「真誠」和「放肆」受到多麼嚴重的混淆!在藝術中,唯有在真誠是經過艱難的辯證所得的結果時,我才會在乎它。
●我們不要輕易相信「前景」,那裡面所有看起來很大的東西都變得特別快。
●在物質世界中,沒有任何事物會完成。一旦我們開始承擔某事,它就會需要我們不斷付出。
●假如我必須提出一個信條,我會說:上帝不是在我們身後的過去,而是在前方的未來。若想尋找祂,我們該看的地方不是生命演化之初,而是它的結束。上帝位於終端,不在初始。
──名家盛讚!撼動世界的一代大師──
紀德是少見能堅持以自傳性風格,來逼視自我內在的作家。他直接挑戰與反叛整個時代所信仰的理性及知識,對於自然的、感官的,以及自由的生命狀態,不斷發出近乎美德般的高亢歌頌語調。紀德想與之勇敢對決的,應是他從小承繼的嚴格清教徒道德觀,以及由科學與理性建構的「絕對」價值體系。──阮慶岳(作家・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教授)
紀德是個無可取代之人,因為他選擇的是「成為」真理。他在年輕時就選擇成為無神論者,而在閱讀紀德日記中的文句時,我們絕不能把它們當作單純的事實說明,即便那是以直陳語態呈現;那些無不是盼望、祈願、敦促、頌揚、懊悔、責難。
經過半世紀之後,他終於真正成為自己心目中的真理,同時也成了我們眾人的真理。從此之後,今天的人們才真正得以成為新真理。──沙特(法國哲學家)
或許我們可以把紀德的《日記》看成是這位文學大師最關鍵的作品。它是一部充滿獨創性的撰述,在諸多層面上大膽逾越當時的主流道德觀——各種性愛禁忌、既定成見、僵化認知、意識形態及宗教禁錮;它時而嚴肅說教、時而妙趣橫飛,深沉穩健中洋溢輕盈不羈,行雲流水間不失緩慢沉澱,無論跨幅或縱深,均超乎所有人的預設。
紀德的日記是一個開放、多元、零碎但不零散的文本……貼近日常,描繪人生的高低起伏、偶然相遇,琴韻、書香,小說創作的契機,對萬般問題的思索──道德、美學、性愛、政治、社會學、宗教……《日記》的結構骨幹是紀德無時無刻不與自己進行的對話。作為思考、辯證、藝術剖析的場域《日記》也為作者建構出一座鏡廳,讓他的創作在那裡自由投射、折射、反射、繞射。──彼得‧史奈德(《紀德日記》編輯、歐洲語言文學學者、「紀德文學獎」評審)
──麥田出版紀德作品──
《如果麥子不死》|對善與美的戀慕對自我最毫無保留的檢視
《遣悲懷》|深情悼亡的經典之作收錄談詩論藝之紀德日記選
《地糧》|掙脫禁錮的驚世名品紀德呼喊解放代表作(即將出版)
作者簡介
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 1869-1951)
二十世紀法國首席文學家之一。父親是巴黎大學法學教授,叔叔是政治經濟學者。家族祖先曾為胡格諾教徒,母親為虔誠天主教徒,家中濃厚的宗教氣息使紀德自小於拘謹保守的教養中成長,卻也奠定他日後轉向企圖拆解教條框架、擁抱個人價值的重要動力。
少年時代的紀德就是愛好讀書、勤於筆耕的少年,二十一歲發表第一部作品《安德烈‧瓦爾特筆記》,隨後幾乎每年都陸續出版新作。一九〇八年參與創建《新法國評論》雜誌,啟發無數後世歐洲知識份子。紀德批判法國對殖民地的剝削、為囚犯人權奔走聲張、投身難民救助慈善工作、對共產思想萌生興趣而訪問蘇聯,始終走在時代的尖端。
一九四七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是「文筆平易近人,充滿文藝氣息,同時也以真誠、無懼的愛及深刻的心理洞見,呈現人類的問題與現況」。同年也獲頒英國牛津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作品廣納小說、回憶錄、評論集、散文集,代表作有《地糧》、《窄門》、《背德者》、《紀德日記》等。自小勤記日記的紀德,晚年致力於畢生日記的整理與出版,其日記忠實展現他求索真理的心靈歷程,被譽為「一部開放、多元、千姿百態的文本」,甚至被視為「一代大師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紀德在作品中私密而坦率地敞開自我,直白述說欲望帶來的牽引與困惑,在當時的歐洲社會中是令人震驚的,使他遭指為異端。甚至在紀德逝世後,羅馬天主教教會仍決定將他的作品列為禁書。他並非僅專營筆耕的作家,更是思想家、道德家,他的每部作品都用以傳達價值的思辨與探究,更屢屢以靈肉拉鋸中的覺醒歷程震撼當世。這位當代的異端份子,卻同時也是後人眼中的先驅者,他自許「以真理之姿溢出時代」,期望人最終應當走向「精神遊牧者」,也成功為後世帶來一股擺脫宗教與道德束縛的思潮,使「人的問題」逐漸凌駕「神的問題」。紀德高貴的誠實始終反映於善與惡的辯證中,他在生活與哲思裡持續質疑,也持續重新定位生存的意義,永遠在如此歷程中尋找新的和諧與完整。正是如此強烈的矛盾為他供給源源不絕的生命動力。
譯者簡介
徐麗松
台大外文系畢業,世紀交替之際旅居法國多年,陸續於巴黎第七大學、里昂第二大學及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修讀語言學及跨文化研究,並在法國及台灣從事英文、法文翻譯及跨界合作工作。
◎導讀|鞦韆上的假面天使 ◎阮慶岳
「紀德是一個敢於指出時代去向、也勇於與全世界為敵的作家,他無懼無悔地坦露自己的私密一切,視本能與現實為真正的真理,但是卻發覺他其實並沒有勇氣與所愛者真正的相互作告白⋯⋯」
◎遣悲懷──就此長存你心
「那時我會自問,如果我們之間的愛在它所有組成元素都已經支離破碎之後卻仍能持續,那麼,它到底是由什麼構成的? 」
◎瑪德蓮日記──如果能為她帶來些許幸福
「她的一滴眼淚都比我的幸福汪洋更深重。」
◎紀德日記選(1889-1923)──靈魂是座展演場
「最美的東西是從瘋狂呼嘯而出,而後用理性書寫而成……作夢時衝向瘋狂邊緣,寫作時盡量逼近理性。」
◎紀德年表
導讀
鞦韆上的假面天使 文/阮慶岳(作家・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教授)
紀德以擅長的告白體所書寫的《遣悲懷》,用來追憶逝去的妻子、也是長他兩歲的表姊瑪德蓮,無疑是優美也誠摯的文學,更是動人心魄、幾乎讓人不忍卒讀的一本懺情書。
他們相知於青梅竹馬的童時,但看似真正促成婚約的動機,卻是因紀德曾經撞見瑪德蓮發現母親與別的男人有染後的哭泣,這讓紀德心生哀憐與保護的心意。然而,紀德完全知道自己性向所在,在詢問了醫師的意見與得到鼓勵後,他毅然開啟了這一段愛與折磨的漫長關係。
這關係以堅強的互信互愛啟始,卻逐漸淪入紀德所寫:「我們之間從不曾嘗試對此做溝通解釋。她本身從未有所抱怨;有的只是一種沉默無語的認份和從未言明的失意。……還有,當痛苦變得無以忍受時,無論是她或是我,我們是如何只能藉由竭力相互疏遠、擺脫對對方的依戀,才得以承受住那種尷尬(我採取的是這個字眼最強烈程度的意義)……」
原本真正相愛的兩人,卻為何會走到這樣的路途去呢?
這也許要從紀德的文學意義談起。紀德是少見能堅持以自傳性風格,來逼視自我內在的作家。他以著類同先知般的使命感與冒險精神,直接挑戰與反叛整個時代所信仰的理性及知識,同時對於個體生命所具有的獨特神祕意義,則高舉著維護其存在可能的保衛態度,因此對於自然的、感官的,以及自由的生命狀態,不斷發出近乎美德般的高亢歌頌語調。
這其中暗示著對於瞬間的存在意義、不確定的一切可能,以及必須持恆堅持的渴望態度,某種積極也絕對的嚮往。其中,紀德想與之勇敢對決的,應是他從小承繼的嚴格清教徒道德觀,以及由科學與理性建構的「絕對」價值體系。他似乎正在建立時代中緩緩甦醒的新宗教,以對存在、個體與本性,致上令人詫異的高度敬意,也藉此控訴有強制意味的集體道德秩序,對於個人思索的不斷凌駕。
紀德有如一個亟欲打倒舊價值體系的唐吉柯德,英姿風發也勇氣畢露。然而相當可悲與戲謔地,他所愛的瑪德蓮卻似乎正是這樣舊價值的代表者,因而總是以一種他自小就熟悉(如同紀德母親般)的優雅、自制及寬大態度,不時來質疑(並包容)他所嚮往的行事路徑,也造成兩人間劇烈的矛盾及苦痛。
紀德以告白式的書寫意圖溝通,卻被瑪德蓮回應說:「假使你能知道那些文字為我帶來的悲傷,你就不會把它寫出來」所擊潰。而在日後自己寫著:「她比我大兩歲,但在某些日子裡看到她時,這個年齡差距卻彷彿是兩代之間的差別。」以及:「我輸了這場遊戲,我放棄了。從此以後,我任憑她去!我也不再愛她,不想再愛她;愛她讓我太痛苦了。我所夢想過的一切,我牽繫在她身上的一切,不都已經屬於過去,屬於萬事終將歸入的墳墓?」
但是,紀德其實又深深依戀著瑪德蓮(以及她所代表的那一切舊價值體系),他因此又寫著:「事實上,她掌控了我的心靈和我的思緒……而且那股力量是她在不自主的情況下散發出來的,因為她向來不會刻意去主宰別人或使人困惑。」
於是,讓自己陷入難以自拔的矛盾深淵裡,只能眼睜睜看著道德與真實(或說舊世界與新世界)的鴻溝,不斷折磨凌虐著兩人間的信任與愛。
一九一八年的夏秋之際,紀德與一個男性伴侶去倫敦旅遊,獨自哀痛在家的瑪德蓮,把紀德寫給她的信件全部燒光。紀德知道後情緒崩潰,在日記裡寫著:「……因此而消失的是我身上最好的那個部分,不再有它可以為我制衡最壞的那個部分了。在超過三十年期間中,我將自己最好的部分給了她(而且仍持續在給),日復一日,再短的分別也不例外。驟然間,我覺得自己毀了。我再也無心於任何事。我不費力氣就可以殺死自己。」
然而瑪德蓮的死去,反而讓紀德見到自己其實的擺盪與矛盾,舊世界的一切不再是罪惡的淵藪與藉口,新世界的神明卻依舊惚恍難明。紀德此時沈痛的回顧自己:「缺少了她的靈魂發出的純淨聲音,我覺得自此彷彿只能在周遭聽到俗不可耐的聲響,混沌、微弱而絕望。……以前,我寫的一切都是為了說服她、引導她的思維。那些文字彷彿構成一段漫長的辯詞;沒有任何書寫像我的作品這般源自如此私密的動機。倘若讀者看不出這點,那就讀不出什麼真正的意義了。」
紀德是一個敢於指出時代去向、也勇於與全世界為敵的作家,他無懼無悔地坦露自己的私密一切,視本能與現實為真正的真理,但是卻發覺他其實並沒有勇氣與所愛者真正的相互作告白。他在瑪德蓮死後寫的《遣悲懷》,以及逐步整理出版的日記,彷彿是要重新彌補什麼缺失的記憶,是一種對愛情的告解、懺情與再宣示。
這些可貴的書寫,同時也是時代在新舊交織辯證、相互撕裂的過程中,對於人類心靈在其間因而顯露的徬徨游移,所提出最直指核心的哀悼與控訴吧!
昨天晚上我想著她,和她說話,就像我過去經常和她說話那樣,而且在想像中比實際當著她的面更輕鬆自在;然後我倏地想到:她已經不在人間了啊⋯⋯有時我確實會到離她很遠的地方,一走就是許多天。但打從孩提時代開始,我就養成向她報告一天的收穫,並在心神中將她與我的悲傷和喜悅聯想在一起。昨天晚上我就是這麼做的,但忽然間我想起來,她已經死了。一切驟然失去了顏色,變得暗淡無光,無論是近來我對一段遠離她的時光所作的回想,或是我回想那些事的那一刻;因為我在思緒中重新經歷那些事,都是為了她。我立刻明白,失去她以後,我的存在也變得枉然,再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現在還活著。我不太喜歡我為了尊重她的謙虛而在我的書寫中替她取的「艾曼紐」這名字。她真正的名字之所以令我歡喜,可能只是因為自小開始,她在我心目中就一直召喚出優雅、溫柔、聰慧和善良的形象。當其他人也取這名字時,我會覺得它彷彿遭到篡奪,我覺得彷彿唯獨她有權利用這個名字。當我為我的《窄門》創造出「艾莉莎」這名字時,那並非出自矯情,而是基於保留。艾莉莎只能有一個。可我書裡的艾莉莎並不是她。我描繪的不是她的圖像。她只是成為我構思女主角的出發點,我不認為她曾在其中認出多少自己的身影。她從沒和我談過那本書,因此我只能推測她讀它時可能有過的思索。那些思索對我而言一直帶著悲痛的色彩,就像一切源自她內心那股深沉哀愁的東西;我是在很久之後才開始揣測出那種哀愁的,因為她那極其含蓄的性格一直阻止她將其顯露、表達出來。我為我的書設想出來的劇情無論再怎麼美,難道它不是在向她證明,面對現實劇碼的我一直是盲目的?想必她感覺自己比艾莉莎簡單得多,比她正常、平凡得多(我的意思是說:比較不像高乃依描繪的女性角色,比較不緊繃)?因為她無時無刻不在懷疑自己,懷疑自己的美麗、優點,懷疑一切為自身光輝、價值造就力量的事物。我相信,後知後覺的我對她的理解終於清楚多了,但在我的愛意最強烈的時候,我對她的誤解居然能深到那般程度!因為我的愛意使勁做的事並非讓我接近她,而是設法讓她接近我發明的那個理想人物。至少這是我現在的感覺,而且我不認為但丁對貝緹麗彩的行為與此有何不同。在她已不在人世的此刻,我之所以企圖重新找到、重新描繪她的往昔身影,那也是──特別是──為了一種做出補償的需求。我不想讓艾莉莎的幽靈遮蔽了她真正的存在。
 「電子信用狀統一慣例」-1.0版 ...
「電子信用狀統一慣例」-1.0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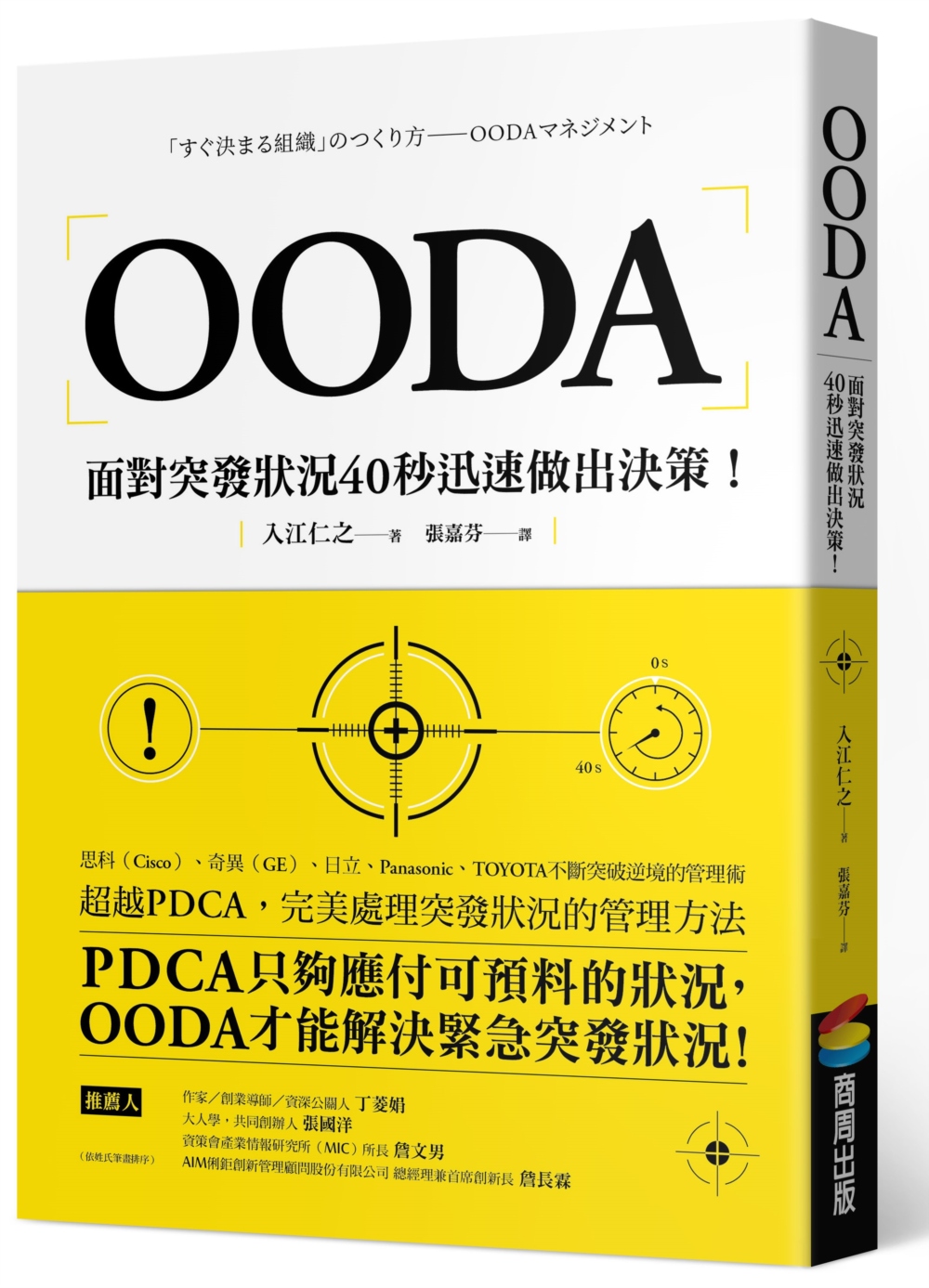 OODA:面對突發狀況40秒迅速做出決策
OODA:面對突發狀況40秒迅速做出決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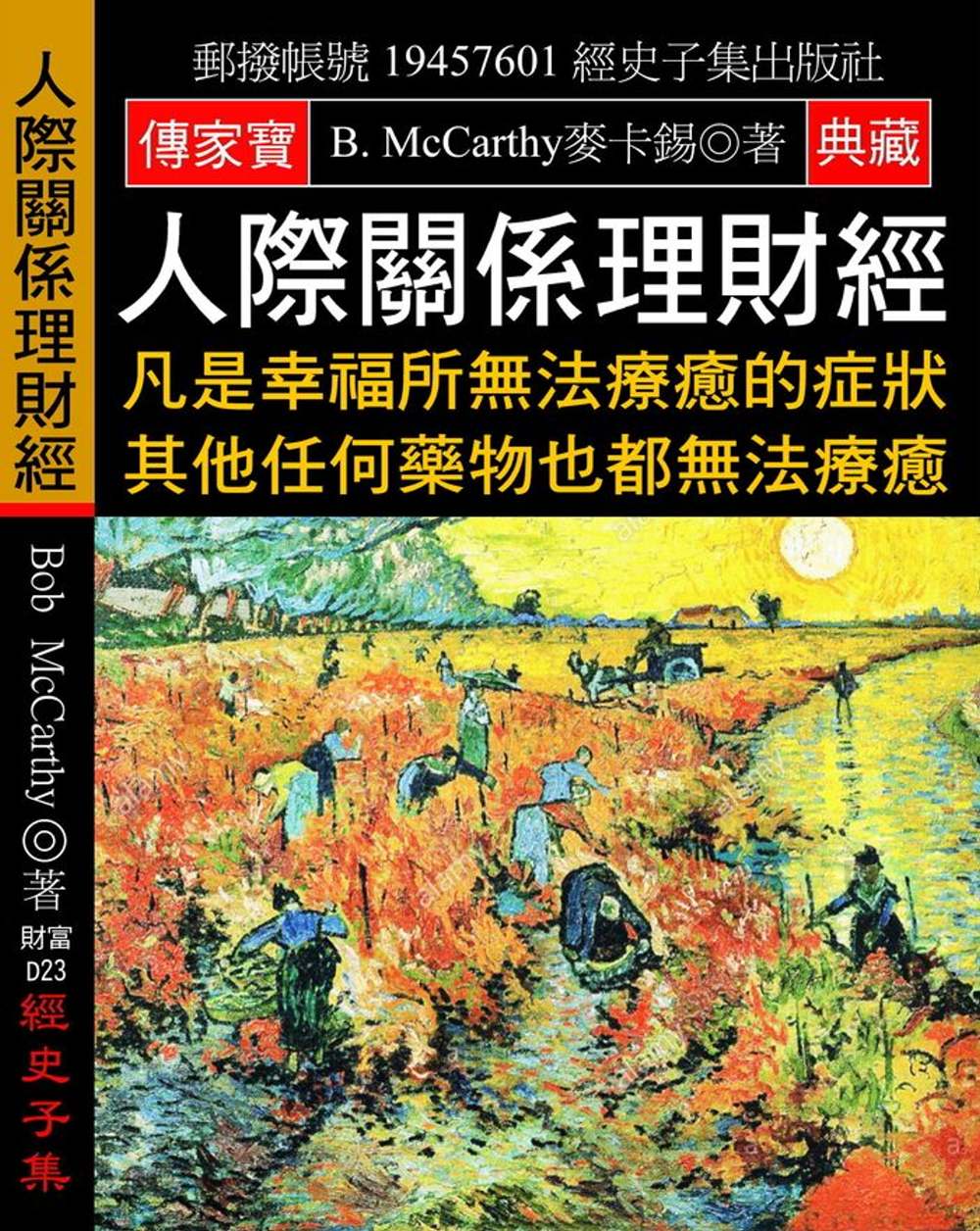 人際關係理財經:凡是幸福所無法療癒...
人際關係理財經:凡是幸福所無法療癒...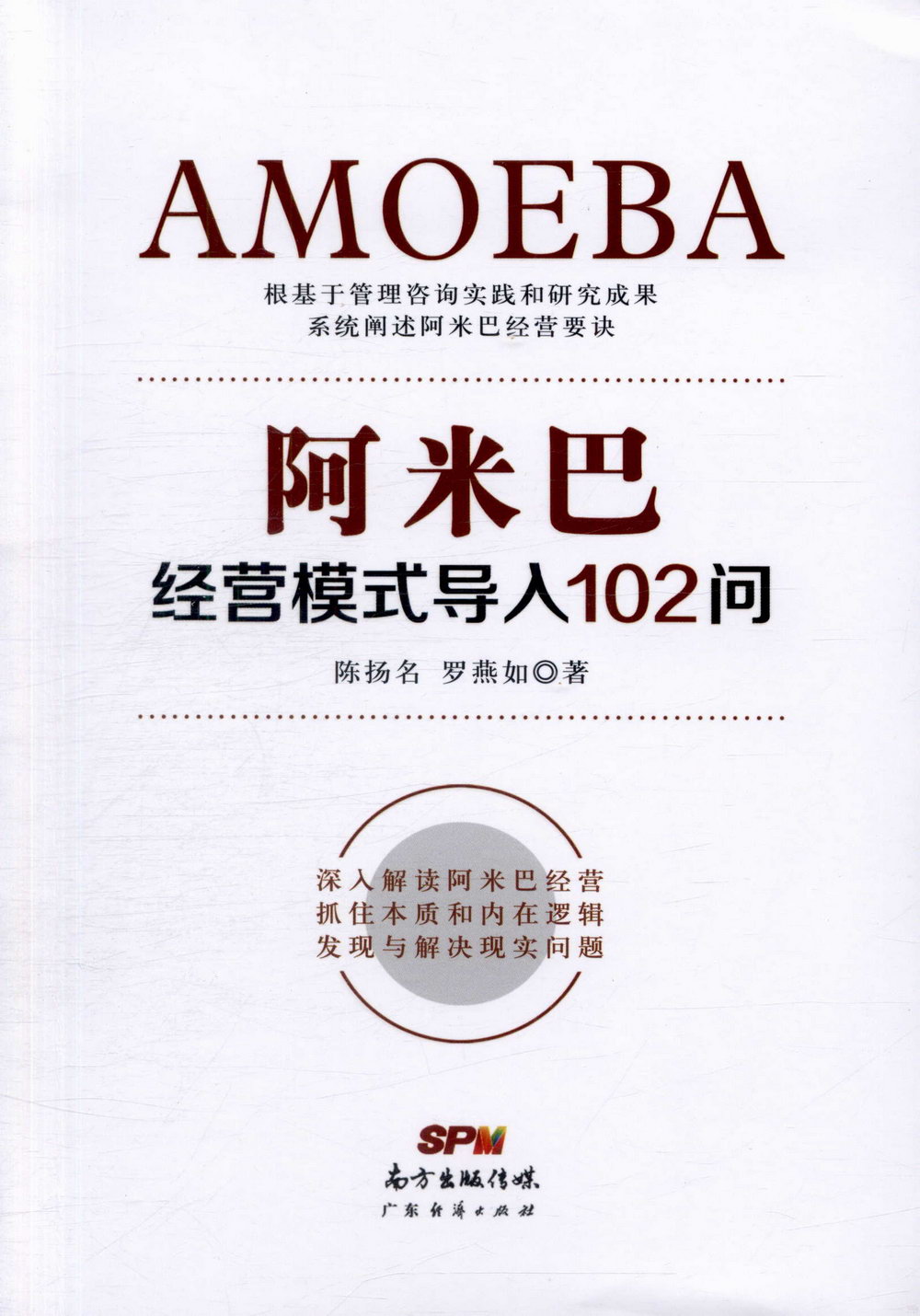 阿米巴經營模式導入102問
阿米巴經營模式導入102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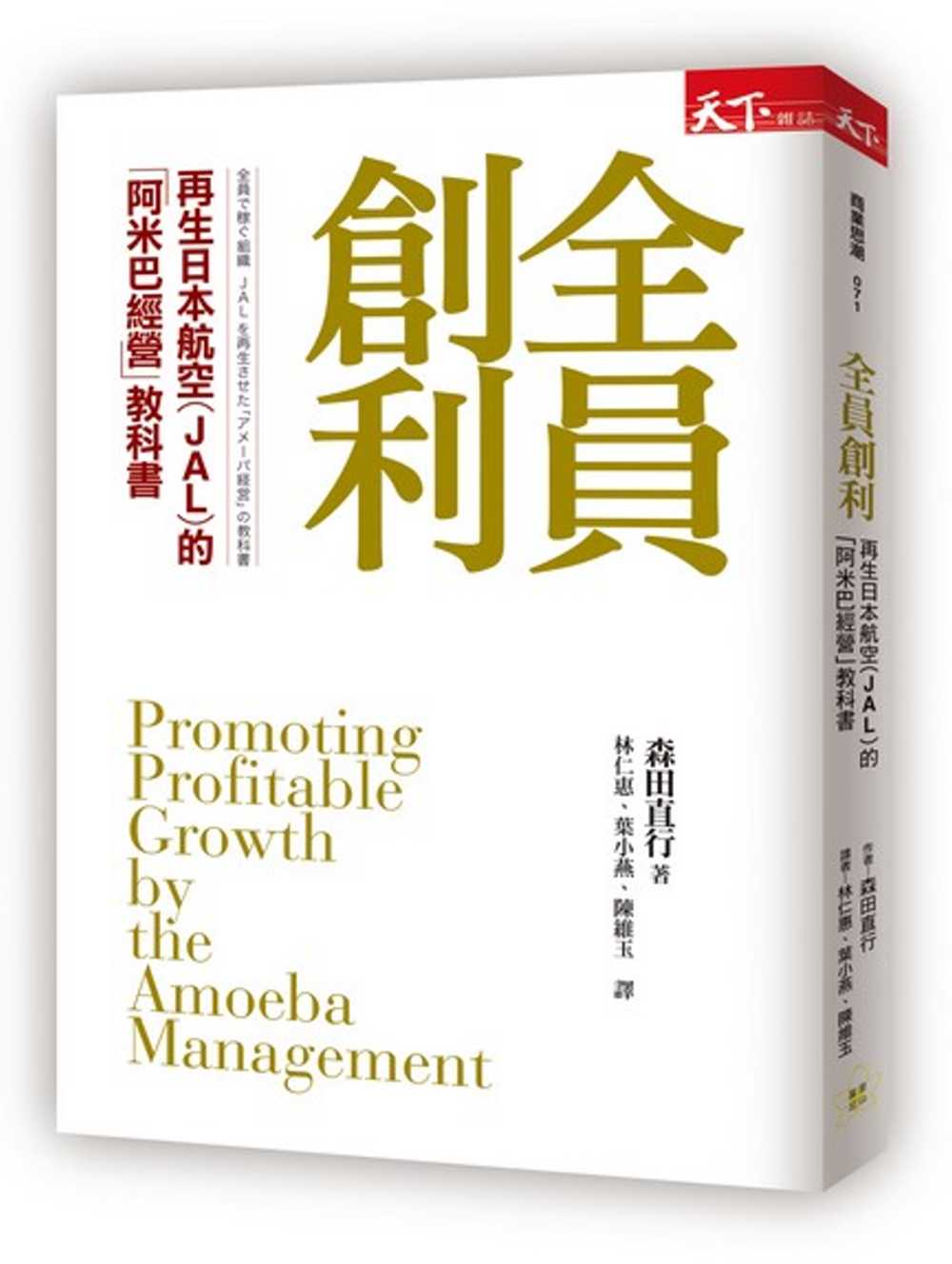 全員創利:再生日本航空(JAL)的...
全員創利:再生日本航空(JAL)的... 跳脫極限:征服內在的恐懼,擺脫現狀...
跳脫極限:征服內在的恐懼,擺脫現狀... 信用狀交易糾紛解析
信用狀交易糾紛解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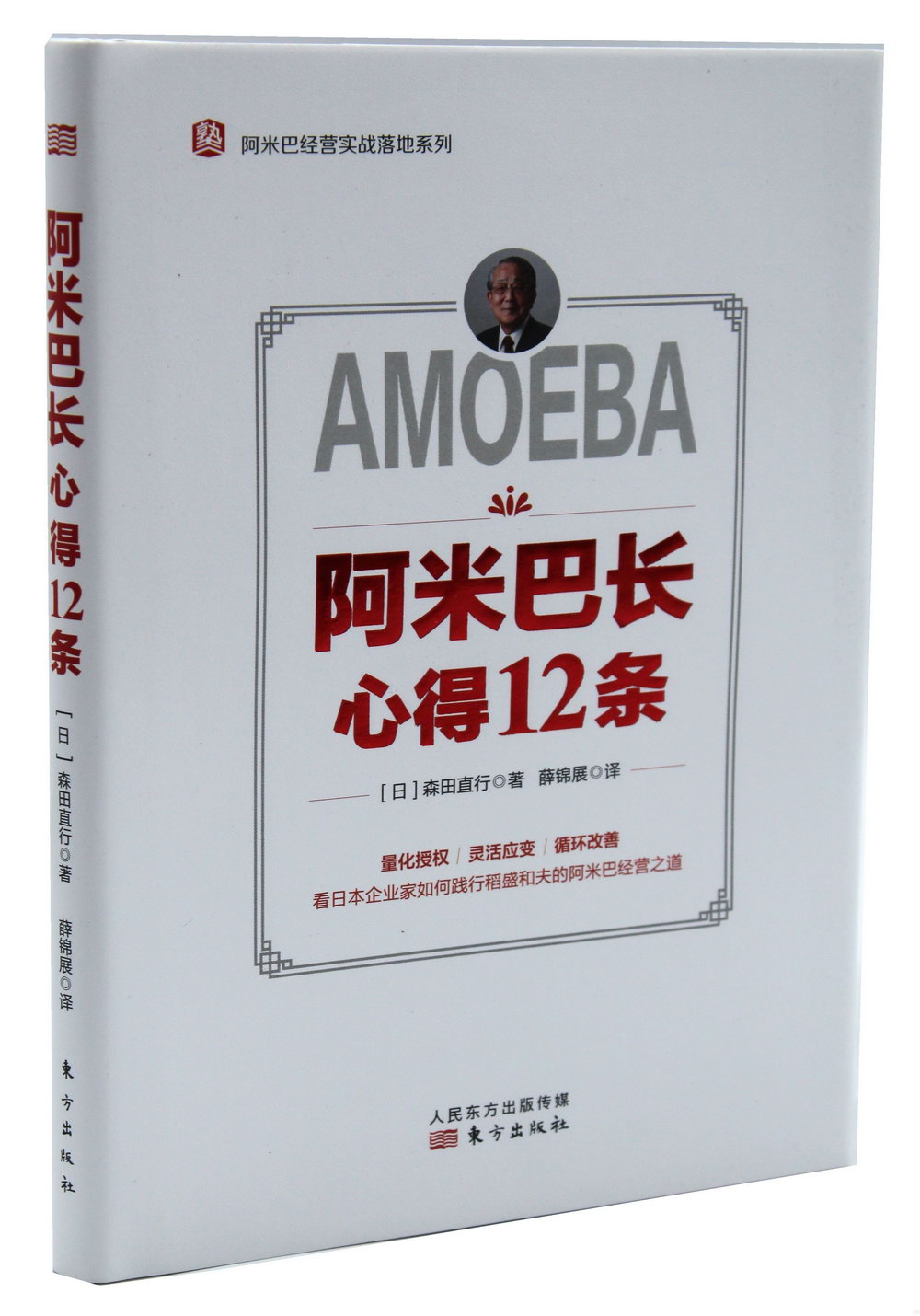 阿米巴長心得12條
阿米巴長心得12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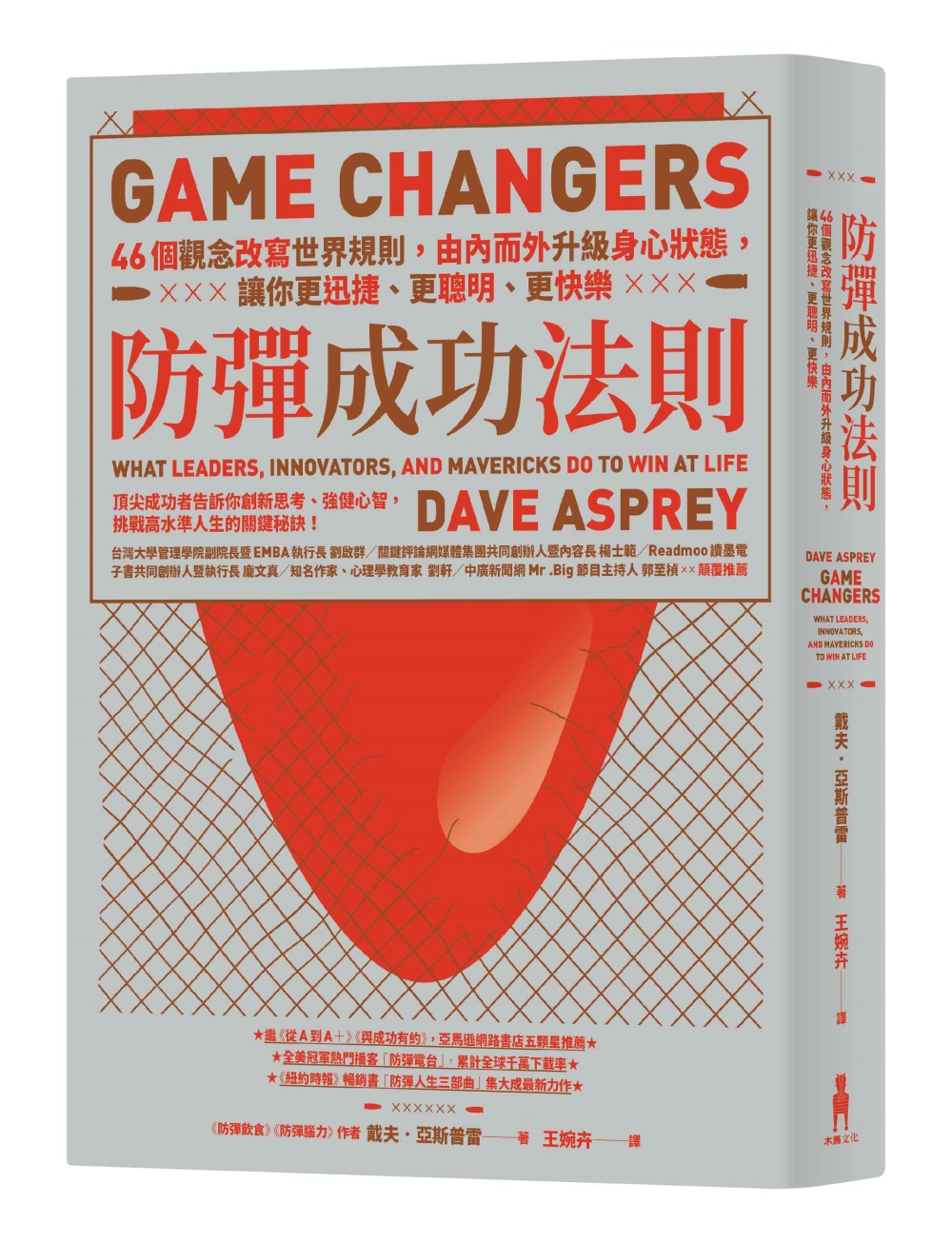 防彈成功法則:46個觀念改寫世界規...
防彈成功法則:46個觀念改寫世界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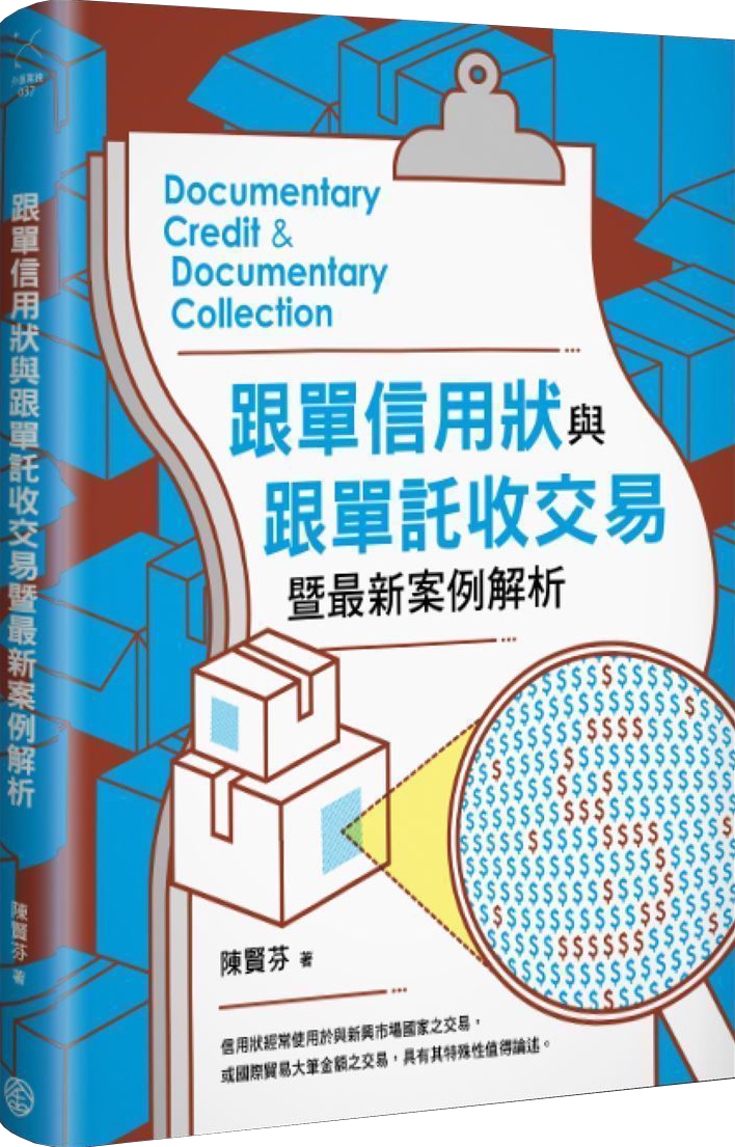 跟單信用狀與跟單託收交易暨最新案例解析
跟單信用狀與跟單託收交易暨最新案例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