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 | 生病了怎麼辦 - 2024年11月

一九八四
遠流╳師大譯研所「經典文學新譯計畫」NO.2
計畫主持人師大譯研所長 賴慈芸
計畫顧問台灣翻譯學會執行長 蘇正隆
在一個語言墮落的時代,作家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在抵抗暴力和承擔苦難上做一個永遠的抗議者。
──喬治.歐威爾
他不怕分離,不怕被出賣,不怕受盡折磨,
他唯一害怕的,是那股讓他不能再愛人的力量。
1945年,歐威爾的《動物農莊》在連續遭到五家出版社拒絕後,終於問世了,立即爆紅成為暢銷書,一輩子幾乎都在過窮苦日子的歐威爾,靠著這本書的版稅,買下了某個偏遠小島的房子,並且在那裡寫出了他更為重要的作品《1984》。
在二十世紀許多重要的文學作品,《一九八四》是難得一見的傑作,因為書中對未來的悲觀假想,隨著時代變得愈來愈真實,也愈來愈讓人無法忘懷。
故事描述在1984年的世界中,大洋國裡每個人都活在「老大哥」的監視下,政府說什麼,人民就得相信什麼,只要言語間透露出一點懷疑或者好奇,就很可能從此人間蒸發。人類生活變成了一個惡夢,而在這惡夢中,有一個可憐蟲試圖尋找個人獨立存在的意義。
溫斯頓.史密斯就是這個可憐蟲。他愛上茱莉亞之後,發現自己的人生不必是如此無聊和死氣沉沉,生命還有各種可能性,包括自由意志。
雖然思想警察能挖出每一個背叛行動,兩人的頭頂上總是有警察監視的眼線盤旋,他們還是開始質疑政府,一步步籌畫計謀,但老大哥無法容忍異議份子,就算只是有念頭也不行,兩個人終究不堪折磨而互相出賣了對方……
歐威爾可說預知了現代生活的情況──無所不在的電視、語言的扭曲,而且還建構出一個如地獄般的駭人世界。本書自出版以來就是學生的必讀讀物,也名列史上最令人心驚的小說之一。
本書特色
★真正全新譯本
★師大翻譯研究所與遠流合作「經典文學新譯」計畫第二本書
★附師大翻譯研究所所長總序、譯者解析文字
★英美中學生必讀書目
★村上春樹為向歐威爾致敬,創作出最新長篇《1Q84》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最喜愛的一部小說
★本書對英語本身產生重大影響,許多經典詞彙,沿用至今
★全球累積銷量破5千萬冊、全球超過62種語言譯本
作者簡介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
本名艾瑞克.亞瑟.布萊爾(Eric Arthur Blair),1903年出生於印度, 1907年隨家人搬回英國, 1917年進入伊頓公學,在學期間即經常投稿到許多大學雜誌。1922至1927年,歐威爾在緬甸擔任印度帝國警察,這段經驗啟發了他寫出第一本小說《緬甸歲月》(1934年出版)。然後他過了幾年窮苦的日子,回到英國之前他先在巴黎住了兩年,在那裡陸續當過私人家教、學校老師和書店店員。
1936年年底,歐威爾加入了西班牙內戰的共和軍,結果受了傷,進入療養院休養,卻再也沒有真正完全康復。二次大戰期間他在英國協助後方備戰工作,並且於1941至1943年間為BBC遠東地區傳播服務工作,後來擔任《論壇報》的文學編輯,同時也為《觀察家》撰稿。1945年,他出版了自己獨樹一格的政治寓言小說《動物農莊》,而這本小說及後來的《一九八四》讓他成為世界知名的作家。
歐威爾是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小說家,由於在緬甸駐紮的五年期間,親眼目睹共產政權對人民的影響,因此他的創作多半傳達對社會不公不義的不滿、諷刺時政,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才是解決之道,而令英國知名評論家封他為「歐洲永恆的良心」。英國泰晤士報則封他為「1945年以來50位最偉大英國作家」第二名。
譯者簡介
徐立妍
師大翻譯研究所筆譯組畢業,譯有《污點》、《以色列:新創企業之國》、《泰絲家的女兒們》,持續翻譯中。
推薦序
雙重科幻小說∕台灣科幻創作推手 葉李華
二十世紀有兩部經典名著《美麗新世界》與《一九八四》,雖然躋身正統文學之林,嚴格說來都是科幻小說,而且皆為「反烏托邦」(Dystopia)這個主題的代表作。
顧名思義,在反烏托邦體制中,一切的一切皆與人類心目中的理想國度背道而馳。而要打造一個反烏托邦,政治力量與科技力量缺一不可,這是撰寫反烏托邦故事的首要潛規則──在《一九八四》中,是以政治力為主、科技力為輔,而《美麗新世界》則恰好相反。
關於政治力量的描寫,本質上即為以社會科學為基礎的幻想(科幻小說中的科學當然涵蓋社會科學),另一方面,在解說科技力量的過程中,作者一定會盡可能發揮科技想像力。因此不言而喻,所有的反烏托邦作品都是雙重的科幻小說。
本書作者早年是社會主義的信徒,曾為了理想參加西班牙內戰,卻因而認清共產主義的真面目。從此他對各種極權主義皆厭惡至極,偏偏又不認同當時的英美政體,使得他對人類社會的前途產生悲觀與絕望,於是在一九四八年,他利用所剩無幾的生命火花,抱病寫出這本不朽的傳世之作。
「老大哥在看著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這句名言幾乎已是本書的同義詞。藉著這句話,作者語重心長地警告當時的讀者,獨裁者為了鞏固權力,一定會無所不用其極地進行滴水不漏的監控。耐人尋味的是,如今極權政治的陰影離世人越來越遠,「老大哥」卻在尖端科技的發展中借屍還魂,對現代人的隱私構成了實質威脅。小至針孔攝影機,大至鋪天蓋地的衛星空照,令人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幾乎可以說,一種另類的反烏托邦已隱然成形……
正因為如此,今天我們仍須對反烏托邦有所瞭解,進而有所警覺,也正因為如此,身為二十一世紀的讀者,仍舊必須將《一九八四》列為必讀的經典──雖然「一九八四」早已成為歷史,《一九八四》永遠不會是過時的預言。
出版緣起
經典文學是人類文化的重要資產,也是人文素養紮根的基礎。
經典文學已成為國外校園指定閱讀,在圖書館借閱前十名的書目中,大半皆屬經典文學。但在台灣卻因為缺乏清晰易讀的好譯本,讓讀者覺得難以親近,久而久之便興趣缺缺。
根據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所長賴慈芸教授的研究,國內目前現有的經典文學譯本存在許多問題,首先在流派上主要是傳承一九三○年代茅盾、李霽野的「歐化派」(強調貼近原文),因此以今日的閱讀標準來看就顯得拗口;其次在出版實務上,早期許多出版社以譯者假名或者不掛譯者的方式,陸續推出經典文學譯本,這是因為當時的政治環境所導致的「不得已」手段,然而到了現代,出版社並未還原譯者的名字,甚至因為譯本互相抄襲刪改,根本已經不知道源頭是哪個譯本了。
可是讀者並不知道這個背後因素,讀到的經典文學都覺得行文艱澀、用詞過時,因而認為經典文學「很難懂、不好讀」。有鑑於此,遠流和師大翻譯所合作進行【經典文學新譯計畫】,欲以貼近當代的語言文字賦予經典文學嶄新面貌,務求人人皆可輕鬆閱讀。
這個計畫已經醞釀了很長一段時間,今年正式開跑進行,也開始討論書單及發譯,譯者皆是經過專業翻譯訓練的譯者,大部分也都是師大翻譯所的學生或畢業校友。今年五月初,遠流及師大翻譯研究所還特別舉行針對譯者的說明會,希望讓每位參加此新譯計畫的譯者都能真正了解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因為譯者不只是語言轉換的文字匠,而是重要的媒介,每個讀者都是透過譯者的詮釋去讀每一本翻譯文學作品,所以譯者一定要對自己翻譯的文本有感情,一如作者對自己的作品投射感情一般。
因此這個計畫的發譯過程也比較特殊,編輯會先通知所有參與計畫的譯者接下來要發譯的書單,然後譯者可以針對自己有興趣、有感情的作品提出試譯請求,接下來試譯完成之後,再由編輯和翻譯所教授決定哪本書是由哪位譯者來翻譯。
譯者除了要翻譯文本之外,還要寫一篇譯序,說明自己的翻譯策略之外,最重要的是,這個文本對譯者本身的意義,我們這麼做的目的就是要突顯譯者的地位,讓讀者感覺到自己正在閱讀的故事是由一個活生生的譯者翻譯出來的,讀者不但閱讀原作者如何安排故事發展的本意,也閱讀到譯者選擇每個字詞的用意,這就是遠流希望能重新翻譯經典文學的意義所在:語言會進化,翻譯也應該跟著進化,每個時代都應該有每個時代的經典文學譯本。
本計畫除九月出版的《大亨小傳》及《一九八四》之外,預定自二0一三年起,每年固定推出八本作品,書單擬定的基礎除了是以作品的經典性為主之外,也希望能納入過去少有中譯本的遺珠之作,讓讀者能更完整認識西方文學的經典樣貌。
【經典文學新譯計畫總序】
聽見譯者的聲音∕師大譯研所所長賴慈芸
想像你今天走進一家書店或圖書館,來到世界文學的專櫃前面。很多作品你都聽過名字,別的書裡也許提過,也許小時候看過改編的青少年版本,也許還看過改編的電影電視版本。但不知為何就是沒有真的讀過全譯本。假設你拿起了其中的一本,但一看左右還有六七種版本呢。那該選哪一本好呢? 比較封面、印刷字體大小、推薦者、出版社的名聲、出版年代、還是譯者?
其實,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譯者。你所讀的每一個中文字都是譯者決定的,每一個句子的節奏都是譯者安排的。每個句子都有不只一種譯法,是譯者決定了用哪種結構,在哪裡斷句,用哪一個詞彙,要不要用成語;也可以說決定了文學翻譯的風格。咦?你也許會問,那作者的風格呢?譯者不是應該盡可能忠實於原作的風格嗎?這就是文學翻譯有趣的地方,也是很多讀者不知道的祕密。
文學翻譯其實是一種表演。就像音樂演奏一樣:作曲家決定了音符和節奏;但聽眾聽到的是演奏家的演出。沒有演奏家會把巴哈彈得像蕭邦,但每一個巴哈的演奏家都有自己的風格,就像每一個蕭邦的演奏家也都不一樣。沒有演奏家,音樂等於不存在。沒有譯者,陌生語言的文學也等於不存在。作者決定了故事的內容,但把故事說出來的是譯者。譯者決定在哪裡連用快節奏的短句,在哪裡用悠長的句子減緩速度。哪裡用親切的口語,哪裡用咬文嚼字的正式語言。譯者的表演工具就是文字。
而且譯者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時空背景、觀點、好惡、語感。也就是說,兩個譯者不可能譯出一模一樣的譯文,就像每一個男高音唱出來的〈公主徹夜未眠〉都有差異。面對同樣的模特兒或靜物風景,每個畫家的畫也都不一樣。就翻譯來說,就算其中某個短句可能雷同,一整個段落也不可能每個句子都選擇一樣的形容詞、一樣的動詞、一樣的片語。五十年前的譯者,不可能和今天的譯者譯出一模一樣的段落;大陸的譯者,也不可能和台灣譯者風格雷同。
而所謂經典,就是不斷召喚新譯本的作品。村上春樹在討論翻譯時曾提出翻譯的「賞味期限」:他說翻譯作品有點像建築物,三十年屋齡的房子是該修一修了,五十年屋齡的房子也該重建了。因為語言不斷在變,時髦的語言會過時,新奇的語法會變成平常,新的語言不斷出現;所以對於重要的作品,每個時代都需要新的譯本。
但台灣歷經一段非常特別的歷史,以至於許多人對文學經典的翻譯有些誤解。很多讀者小時候看的經典文學翻譯,是不是翻譯腔很重?常有艱深而難以理解的句子?根本不知道譯者是誰?即使有名字,也不知道是男是女,年紀多大?有些作品掛了眾多名人推薦,但書封書背版權頁到處都找不到譯者的名字? 甚至於書上有推薦者的生平簡介,卻毫無譯者簡介,彷彿誰譯的不重要,誰推薦的比較重要。為什麼會有這些怪象?
這是因為從戰後至今,台灣的文學翻譯市場始終非常依賴大陸譯本,依賴情形可能遠超過大多數人的想像。台灣在戰前半世紀是日本殖民地,普遍接受日本教育,官方語言是日文;漢人移民以閩粵原籍為主,日常語言是台語和客語,影響現代中文甚鉅的五四運動發生在日治時期,台灣並沒有親歷五四運動,中文私塾教的還是文言文。也就是說,戰後大陸接收台灣時,台灣人民在語言上面臨極大的困難。中華民國國語根據的是北方官話,對台灣居民來說已經是全新的語言了;五四運動後提倡我手寫我口,不會說就不會寫,因此台灣人的白話文也寫不好。至於翻譯,民初還有文言白話之爭,一九三O年代以後白話文翻譯已成主流,對於國語還講不好,白話文還寫不好的台灣人來說,要立刻用白話文翻譯實在不太容易。因此除了少數隨政府遷台的譯者之外,依賴大陸譯本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如果不是受到政治因素干擾,本來也沒有太大問題。我們也沒聽說過美國讀者會拒絕英國譯者的作品。
問題出在戒嚴法。1945到1949年間,已有好幾家上海出版社來台開設分店,把大陸譯本帶進台灣。但1949年開始戒嚴,明文規定「共匪及已附匪作家著作及翻譯一律查禁」,由於隨政府遷台的譯者人數不多,絕大部分的譯者遂皆在查禁之列。這些查禁若嚴格執行,台灣就會陷於無書可出的窘境,因此從1950年代開始,一些出版社開始隱匿譯者姓名出版。啟明書局每一本譯作皆署名「啟明編譯所」翻譯,新興書局則會取一些「卓儒」、「顧隱」等假譯者名,大概是取「著名學者」和「因故隱之」之意。1959年內政部放寬規定,將查禁辦法改為「附匪及陷匪份子三十七年以前出版之作品與翻譯,經過審查內容無問題且有參考價值者可將作者姓名略去或重行改裝出版。」,等於承認上述手段合法,因此後來各家出版社紛紛跟進,「林維堂」、「胡鳴天」、「紀德鈞」等假譯者皆有甚多「譯作」,最多產的譯者則要算「鍾斯」和「鍾文」了,可以從希臘荷馬史詩、阿拉伯文的天方夜譚,中古的神曲,翻到法文的大小仲馬、英文的簡愛,甚至連海明威和勞倫斯都可以翻譯,真是無所不能。書目中登記在「鍾斯」名下的經典文學超過二十部,相當驚人,而且這兩個名字還可以互換,有些版本是「鍾斯」的,再版時卻改署「鍾文」,更添混亂。
因此,在「本地翻譯人才不足」及「戒嚴」這兩大因素之下,台灣的經典文學翻譯簡直成了一筆糊塗帳。解嚴前的英美十九世紀前小說,大概有三分之二是大陸譯本,法文、俄文的比例可能更高。而且因為這個不能說的秘密,譯者完全被消音了。最具譯者個人色彩的譯者序跋常常會留下破綻,例如1969年出版的《西線無戰事》,譯者序居然出現「譯者做這篇序的時候,華北正在被人侵略」字樣,匪夷所思(其實這篇譯序是錢公俠1936年在上海寫的,一點也不奇怪);或是書名明明是《金銀島》,序卻寫「這本《寶島》…」(因為抄的是顧鈞正的《寶島》,編輯忘了改序)。因此後來比較聰明的出版社多半拿掉原譯序,以免露出破綻;有些還會用介紹作者作品的文字作為「代譯序」,或放些作者照片,希望讀者完全忘記譯者的存在。在這種作法之下,譯者不但名字遭到竄改,連個人翻譯的心聲看法也一併被消音了。
戒嚴期間依賴大陸譯本的情形,還不限於1949年以前的舊譯。事實上,1950年代的大陸譯本仍源源不絕地繼續流入台灣市場(可能是透過香港),當然也是易名出版。到1958年以後,因為大陸動亂,譯本來源中斷了20年,下一波引進的大陸譯本是文革後作品,1980年代的「遠景」、「志文」都有不少文革後新譯本,但彼時台灣仍在戒嚴期間,所以也還是以假名出版。1987年解嚴之後,才逐漸有出版社引進有署名的大陸新譯本。這個時期雖然有些版權頁會註明譯者是誰,但出版社似乎仍不希望讀者知道這是對岸作品,也不強調譯者,多半請本地學者及作家寫導讀和推薦文章,譯者的聲音還是極其微弱;甚至有些譯作,列了一大堆推薦序,就是不知道譯者是誰。加上原來的假譯本也沒有立即消失,仍繼續印行十餘年,今天還可以買到,更別說各圖書館書目及藏書也都沒有更正,研究者仍繼續引用錯誤的資料,譯者的聲音仍然沒有被聽見。
因此,今天這套書的意義,不只是「又一批經典新譯」而已。我們還希望讀者可以聽見譯者的聲音。每一個譯者都會以表演者的身分,寫下譯序。他們也是讀者,有自己的閱讀經驗,有自己的偏好;他們知道自己的翻譯不是第一個,可能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但他們的譯作是在今天的台灣出現的,有今日台灣的語言特色,不同於其他時候和別的地點。過去匿名發行舊譯的年代,不少譯作是1940年代的作品,除了有語言過時的問題之外,翻譯策略偏向直譯,也是一大問題。比較起來,1920年代的作品雖然較早,其實比較易讀。以前課本收錄的幾篇翻譯作品,如胡適譯的《最後一課》和夏丏尊譯的《愛的教育》,就都是1920年代作品。但由於戒嚴期間盲目改名出書的結果,台灣經典翻譯以1940年代的直譯為最多,造成文學作品就是翻譯腔很重,很難讀的普遍印象。我們希望透過這一批的新譯,一方面是讓譯者發聲,有清楚的「生產履歷」,讓讀者意識到你所讀的是譯者和作者合作的成果;一方面也希望除去「文學作品都很難讀」的印象,讓讀者可以體會閱讀經典的樂趣。
閱讀世界經典文學是人文素養的一部分,但一種外語能力好到可以讀原文的文學名作談何容易,遑論三、四種以上的外語。英國的企鵝文庫、日本的岩波文庫、新潮文庫等皆透過譯本,為其國人引進豐富的世界文學資產。英美作家常引用各國文學作品;村上春樹、大江健三郎這些著名作家,也常常在散文中提起世界文學的日譯本。但台灣的文學翻譯有種種不利因素,首先是前述的譯本過時、譯者消音現象;再來是英文獨大,很多人看不起中文譯本,覺得要讀就要讀原文(即使是英文譯本也強過中文譯本);再來就是升學考試壓力,讓最該讀世界文學的學生往往就錯過了美好的文學作品,未來也未必有機會再讀,極為可惜。我們希望藉著這套譯本,為翻譯發聲,讓大家理直氣壯地讀中文譯本;也讓台灣的學生及各年齡層的讀者,有機會以符合我們時代需求的中文,好好閱讀世界文學的全譯本,種下美好的種子。
譯者序老大哥就是你 徐立妍第一次讀到《一九八四》是大學的時候,也不知道在哪本科普書上讀到這本書的書名,一時興起就跑到圖書館去借閱,那個時候其實還看不太懂,闔上書頁就這樣過去了,只是後來看到「老大哥」這三個字,我可以告訴人家這是從《一九八四》中來的。再一次接觸到《一九八四》,我從讀者變成了譯者,我對以前那個譯本已經沒什麼印象,但是這次讀起原文,我覺得《一九八四》的語言其實一點也不一九八四,完全沒有年代久遠的感覺,或許是因為歐威爾所建構的世界實在太超乎現實,不但重新劃分國家疆界,在語言上也大膽設計出一套新語(newspeak)系統,所以不管什麼時候讀,都不會顯得老舊。台灣最早的《一九八四》譯本出現在民國四十一年,譯者是王鶴儀先生,這個譯本目前只有在圖書館才能翻閱,後來的譯本也有如鈕先鍾、萬仞(疑為假名),及彭邦楨的版本,但是民國七十年出現邱素慧翻譯的版本後,其他版本就漸漸消失了,我大學時代讀的版本想必也是邱素慧的譯本,為了寫這篇譯序,我又重新讀了這個譯本,唯一的問題大概就出在語言的時代感,畢竟已經是三十幾年前的譯本,許多用字遣詞現在讀來有些拗口,尤其是人物的對話。例如溫斯頓和茱莉亞第一次在樹林中幽會,兩人有這樣一段對話:”I hate purity, I hate goodness. I don’t want any virtue to exist anywhere. I want everyone to be corrupt to the bones.””Well, then, I ought to suit you, dear. I’m corrupt to the bones.”邱素慧的譯文在民國七十年或許聽起來很合適:「我恨純潔無瑕。我恨完整無缺。我不需要任何道德,更不需要它存在任何處。我只要每人的骨頭都腐蝕掉。」「我該使你滿足,親愛的。我的骨頭正在腐爛呢。」不過說真的,現在說到「骨頭都腐蝕掉」,可能只有CSI影集才會出現了,所以我的處理方式就選擇貼近現代口語:「我討厭純潔,我討厭善良!我不希望這個世界上有美德。我希望每個人都爛到骨子裡。」「喔,這樣的話,我應該很適合你,親愛的。我就是爛到骨子裡了。」我在翻譯每句對話的時候都會自己唸唸看,如果唸起來感覺很彆扭,就會改變譯法,甚至有時候會幻想某個演員來唸這段對話,自己想像如果電視上播出這段戲的話,我會不會覺得台詞寫得很爛。(是的,我想很多,不過這招對我很有效。)其實翻譯《一九八四》最大的挑戰是要先理解溫斯頓的思考邏輯,還有大洋國英社黨的統治概念,否則有許多獨白或宣傳口令都很難抓到語氣。翻譯接近完稿階段時,正好遇上北韓前領導人金正日逝世的新聞熱潮,新聞媒體無所不用其極挖掘消息,盡量「深入」報導北韓國內情況,很多報導內容之荒謬會讓人很難想像世界上還有這樣的國家,但是比對《一九八四》的內容,就讓人不得不佩服歐威爾的真知灼見,他居然能在一九四八年就塑造出一個這麼荒謬又寫實的極權國家,這是多麼震撼的一記警告,他創造出「老大哥」這樣的人物,現在也成為極權政治的代名詞,還記得今年三月爆發的台北市士林文林苑都更案爭議,王家的房子遭到強行拆除後,周圍圍起了鐵板圍欄,有人在鐵板上用噴漆畫了一顆大眼睛,旁邊寫著: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老大哥在看著你。)抗議政府一意孤行的行動,看著稍早警察驅逐抗議民眾的畫面,不免讓人心底發毛,在老大哥所統治的大洋國內,黨就是一切,老大哥「看顧」著所有人,他的命令沒有轉圜的餘地。不過歐威爾大概沒有想到網路會在短短六十幾年間迅速發展,他寫《一九八四》的時候還是用打字機一個字一個字敲出來的,現代的作家在電腦上寫稿,要刪要改都容易多了,而且網路的力量也是另一種「老大哥」的體現,《一九八四》的世界裡,人與人之間接觸不多,也沒有其他管道得知別人的消息,溫斯頓從頭到尾都不知道茱莉亞的姓氏,只有黨和老大哥才能夠知道所有人的一切細節。現在有了網路的力量,要「人肉搜索」一點也不難,上傳一張照片或一段影片,幾小時後就能收到回覆,知道影中人的身分;你以為在網路上可以隱匿身分,其實透過IP或其他管道還是可以追蹤到本人,歐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把監視工具叫做「電屏」(telescreen),在現代我們稱之為「網路」。每翻譯一個字,我都能感覺到「老大哥」真實的存在。歐威爾抨擊極權政府壓迫人民,實行高壓統治,人民只能依循老大哥認可的規範生活行事,老大哥的眼睛隨時隨地監視著每一個人;而我,雖然不是生在極權統治的國家,但是仍然感受到無數雙眼睛透過網路監視著我,當我翻譯到這句:「老大哥正在看著你。」我看著電腦上開著網路瀏覽器視窗,想著:「不,老大哥就是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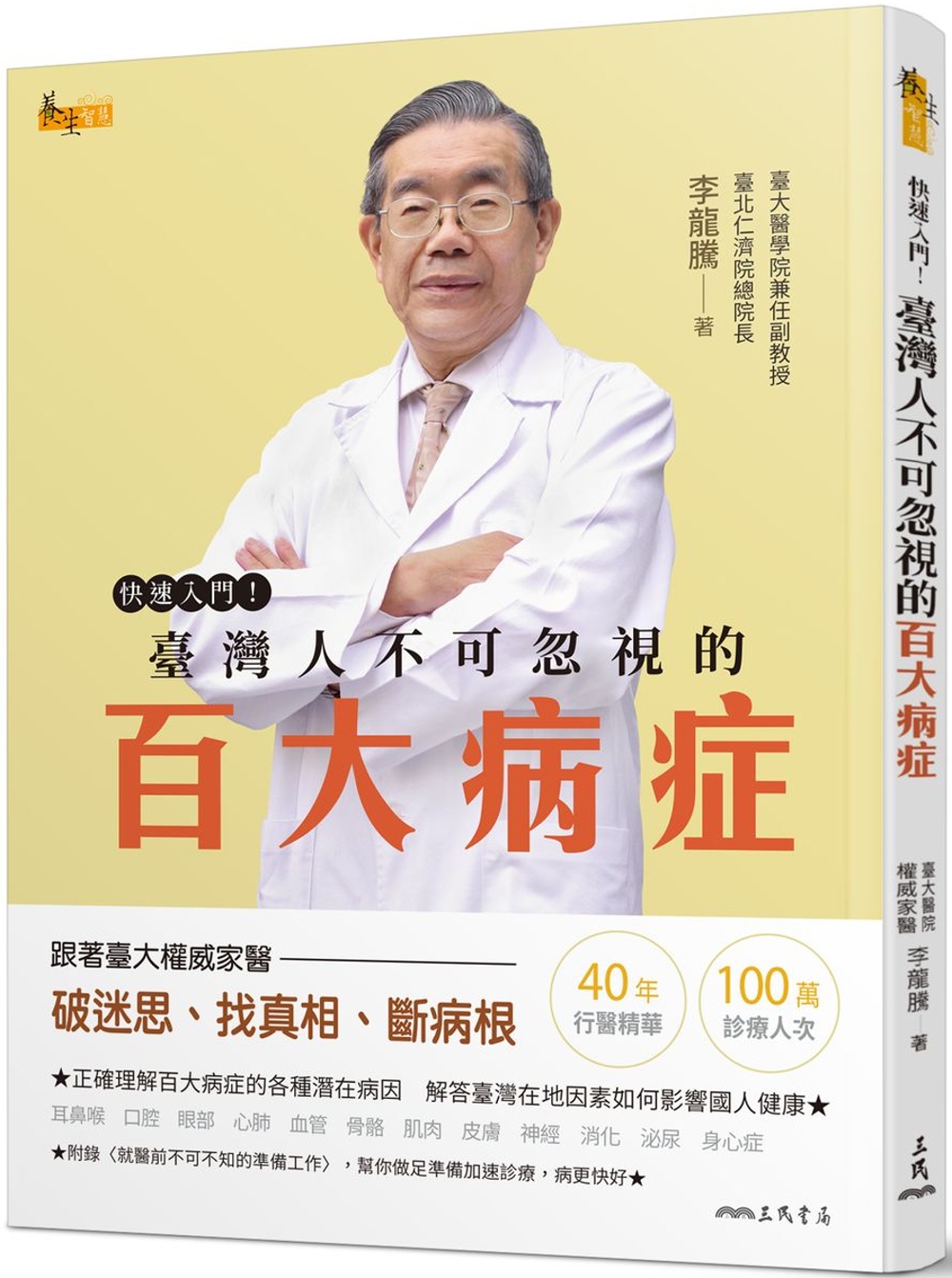 快速入門!臺灣人不可忽視的百大病症
快速入門!臺灣人不可忽視的百大病症 小心!別讓腸癌找上妳:顧好腸胃,遠...
小心!別讓腸癌找上妳:顧好腸胃,遠... 防癌抗癌靠自己:西醫不說的養生新觀念
防癌抗癌靠自己:西醫不說的養生新觀念 大腸直腸癌關鍵50問
大腸直腸癌關鍵50問 排便異常&大腸瘜肉&痔瘡&腸躁症健...
排便異常&大腸瘜肉&痔瘡&腸躁症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