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雪 上 | 生病了怎麼辦 - 2024年11月

細雪 上
惡魔作家的女兒國,陰翳深處的芍藥圃,谷崎潤一郎織錦蒔岡家四姊妹優雅燦爛,而瀕臨潰滅的人生。一幅巨大奢侈的長篇人間畫軸,展讀如櫻花凋落的末世華麗。日本文學大師 林水福 全新精譯《細雪》問世六十年,唯一繁體中文正式授權版
惡魔作家的女兒國,陰翳深處的芍藥圃。
誕生於日本戰爭存亡之際的《細雪》, 谷崎潤一郎站在時代背面, 以碎玉撒落銅盤的精緻觸感, 寫下對於優雅貴族世界行將消逝的懷念。
蒔岡家姊妹們的四季比其他人更像夢境。
春日盛裝,讓粉淚櫻雪墜落於髮鬢與袖口, 或在夏夜撲捉流螢,如金色時光消逝在蒼白的指端…… 傳統之美是同徐徐打開的摺扇,拂來芬芳稀微的風。
那些端莊的儀式、姿容與用語, 正是對於舊日世界的回眸,如金鷓鴣, 在硝煙與沙塵中拖長了反光的尾羽。
活在新舊文化交替之處,這種美麗, 以及對美麗的堅守,完全是奢侈。
還有什麼比瀕臨崩潰的優雅更為燦爛的?
《細雪》正是以無窮細節堆積起來的, 懸崖貴族平金織錦的長篇畫軸。
西元一九三○、四○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繁盛,大阪的經商世家在蘆屋地區落土扎根,這群上流世族奉持著傳統開懷擁抱新式文化,過著東西交雜的綺麗生活。
大阪船場家的蒔岡姊妹便是帶著傳統優勢,展開她們的豐富人生。
二姊幸子於結婚後與丈夫搬至蘆屋,與大姊鶴子丈夫不合的三妹雪子、么妹妙子在本家與二姊蘆屋家交替居住。幸子與丈夫貞之助與女兒悅子,是令人欣羨的模範家庭,同時也是妹妹們的最佳避風港。
幸福人妻幸子眼見雪子已過適婚年齡,與丈夫兩人積極為其物色合適對象,而另一方面妙子飛蛾撲火的愛情也讓家人們頭痛,生怕蜚短流長影響雪子的婚姻之路,故事便在雪子一次次的相親中展開……
小說中對於姊妹們的美貌以及迥異個性,有細緻的描寫,而夫人們身穿合服出席家庭音樂會、賞櫻、捕螢的悠閒時光,也是當時上流人家生活的寫真。
作者簡介
谷崎潤一郎
明治十九年生於東京日本橋(1886~1965)。東京帝大國文科肄業。明治四十三年與小山內薰等創刊第二次《新思潮》,發表〈刺青〉、〈麒麟〉等,受永井荷風激賞,確立文壇地位。最初喜歡西歐風格,關東大震災後遷移到關西定居,文風逐漸轉向純日本風格。以《痴人之愛》、《卍》、《春琴抄》、《細雪》、《少將滋幹之母》、《鍵》等展開富麗的官能美與陰翳的古典美世界,經常走在文壇的最高峰。晚年致力於《源氏物語》的現代語翻譯。《細雪》獲每日出版文化賞及朝日文化賞,《瘋癲老人日記》獲每日藝術大賞。一九四九年並獲頒文化勛章。一九六四年被選為第一位獲得全美藝術院榮譽會員的日本作家。
譯者簡介
林水福
日本國立東北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臺北文化中心主任。曾任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外語學院院長暨副校長、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院長暨日文系主任及所長、日本國立東北大學客座研究員、梅光女學院大學副教授、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理事長、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理事長。著有《源氏物語的女性》、《日本文學導遊》、《讚歧典侍日記之研究》(日文)、《他山之石》、《日本現代文學掃描》、《中外文學交流》(合著)、《源氏物語是什麼》(合著);譯有谷崎潤一郎的《鍵》、《卍》、《痴人之愛》,遠藤周作的《深河》、《醜聞》、《武士》、《沉默》、《海與毒藥──遠藤周作中短篇小說集》、《我.拋棄了的.女人》,井上靖的《蒼狼》,及□原登《飛翔的麒麟》(上、下)、《家族寫真》等書;評論、散文、專欄散見各大報刊、雜誌。
《細雪》中文版序文(山口政幸∕專修大學教授)細雪內文
序
小說的主要舞臺──蘆屋,是大正時期(一九一二 ~ 二六)於大阪經商成功的商人所全新開發的住宅區。這座城鎮裡有以大阪梅田為起點的阪急.阪神兩條鐵路通過,依山傍海風光明媚,甚至於戰後實施日本國內前所未有的「豪宅條例」,成為首屈一指的高級住宅區。尤其是靠近山區且視野遼闊的地帶,吸引不少人在此興建豪宅。蘆屋於《細雪》日文原文裡雖然是寫成「蘆屋」來表示,但於現今日本則是標記成「□屋」。昭和十五年(一九四○)蘆屋升格為市,這一年剛好與小說後半情節發展的時期相疊合。
蒔岡四姐妹一家人當初會從大阪船場這處歷史悠久的批發商店街,搬遷至同樣是位於大阪的上本町內,主要是父親晚年「趕上住宅和店鋪分開的潮流」。長女鶴子對外招贅丈夫,讓蒔岡一家能夠繼續傳承下去。然而,丈夫辰雄卻放棄蒔岡家代代相傳的家業(奇妙的是作品裡對蒔岡的家業從未有明確的描述),而於銀行工作。之後,辰雄晉升為東京丸之內的支店長,決定將一家搬至東京澀谷定居。在大阪的本家裡,未婚的三女雪子及四女妙子則因為跟姐夫之間的相處關係不佳,經常拜訪二女幸子位於蘆屋的住處,不知不覺中則在蘆屋這邊住了下來。蘆屋的房子當初也是掛著蒔岡的名義,可看做是蒔岡家的另一個分枝。幸子與會計師的丈夫貞之助,以及即將上小學的女兒悅子一起在這裡生活。生性原本就喜歡熱鬧的幸子,對於兩位妹妹把蘆屋這裡當做是本家而住下來的這件事,雖然心中對本家感到有些顧忌,但仍是打從心底愉快地接受這兩位妹妹。與擁有喜愛傳統舞蹈、製作人偶等多樣興趣且個性活潑的妙子完全不同,內向的雪子把姪女悅子視如己出,從全心全力照顧姪女的過程中,獲得不少喜悅。年歲即將邁入三十大關的雪子,試過幾回相親,可惜沒一次成功,而錯失婚期。另一方面,妙子則是跟在船場地區經營貴金屬買賣的奧□家三少爺──啟三郎兩人有著一段維持五六年之久,像是孽緣般的關係。幸子在丈夫貞之助的理解和協助之下,為兩位妹妹(特別是未曾對自己的婚事上表現積極態度的雪子)的婚事奔波勞碌。同樣的,幸子也對妙子的戀愛對象每次總像奧□那樣不甚登對,而打從心底感到煩惱。幸子雖然對兩位妹妹不順利的愛情抱持過度的同情及憐憫,有時也會由於兩位妹妹出乎意料之外的失態與行動,感到「胸口好像被刺了一下」。儘管如此,她對妹妹們以及搬去東京居住的長姐依然維持不變的手足之情。而丈夫貞之助則能理解妻子以維繫自家姐妹之情為重心的生活,並長久以來支持妻子的行動。幸子、雪子、妙子三姐妹外表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要年輕許多,三人有許多共通處,但也各自擁有不同的長處,給外人三姐妹感情很好的印象。
幸子在作品中佔有相當的分量,其身邊的人際關係大致如上所述。當我們把焦點轉移到她位於蘆屋的房子上時,會發現蘆屋的房子與大阪上本町舊家昏暗的氣氛相比,有非常大的差距。此外,蘆屋的房子也跟長姐搬遷至澀谷的家不同,完全沒有東京新興住宅所呈現出來的平凡庸俗感。一年四季綻放美麗花朵的庭院裡,陽臺上放著白樺樹做成的椅子。庭院的隔壁,則是住著遠從德國來的一家人,兩戶透過小孩的互相往來,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客廳裡,暖□內則是燃燒著柴火,還擺著一架鋼琴。一家之主則是在晚飯結束之餘,於茶几旁品嚐年代久遠的白葡萄酒以及起司。在這裡,跟法籍老師學習法文會話,或是姐妹們打扮得風光體面,一同出席著名海外鋼琴家的小型演奏會,都是習以為常的日常風景。換句話說,在戰前的日本社會裡,去除貴族與財閥等特權階級之後,唯有在極少數的富裕中產階層才可見到這種不受古老秩序束縛,且悠閒舒適的歐化生活樣式。不單如此,這裡的生活同時也保留著深厚的日本獨特傳統習慣、風俗、技藝等。對蒔岡家的姐妹而言,影響這些日常生活的樣式並非來自當時被視為生活指標的「帝都」(即東京),而是來自於地理面積範圍相對狹窄卻急速現代化的阪神地區。在此,千萬不可忘記蘆屋與當時對外開放的港口──神戶之間有著相當接近的距離。明治維新(一八六八年)後經過將近七十個年頭的歲月流逝,歐美文化從神戶居留地業已確實地滲透至庶民階層的生活當中。蘆屋儼然成為一處連結西化的神戶以及傳統的大阪的交界處。
這一點,我們亦可從幸子身邊的人際關係中得到相同的印證。為雪子介紹結婚對象的人物是幸子經常光顧的美容院老闆娘,或是一同於女學校就讀的朋友,這些人可算是代表神戶山手地區領先接受歐化又擁有閒暇時間的階級。另一方面,幫忙搬遷或是照顧病人的人物,則是昔日就在蒔岡家有深厚主從關係的傭人,或是像阿春那樣宛如成為家族一員的女僕。跟前者相比,後者對蒔岡一家的忠誠是值得信賴且不會受到任何動搖。他們對於施予恩義之情的蒔岡家,是絕不會做出任何違背本家或主人意思的事情,遑論會有什麼背信忘義的行為。幸子非常瞭解這些,這是因為她熟知生存於舊秩序社會裡人們的個性。這個部份可以由雪子相親的過程中輕易地看出來。一同跟著雪子的相親對象前來,自稱為「常董」的中年紳士,就算他擁有著顯赫的頭銜,幸子仍毫不遲疑地認為這位中年紳士就是那種舊式商店裡一定會有一兩位「善於討主人歡心或逗主人笑的掌櫃或二掌櫃」。這個時期,正也是古老傳統的商店透過股票上市,轉換蛻變成全新公司組織的時代。儘管如此,幸子卻可以快速地從自己昔日在本家生活的經驗當中,看出對方身上散發出來的氣質及本性。
換句話說,能讓幸子迅速做出判斷的背後裡存在一個大前提,那就是:無論資本主義經濟如何一點一滴的改變舊有社會價值觀,以及鬆動由年功序列堆砌出來的社會制度,但是蒔岡姐妹們的內心裡面,要求下人們應該遵守的道德標準並未因此受到任何影響或是有所改變。就算幸子每日過著上述接受西方文化的時髦生活,當稱呼她自己時會使用「御寮人樣」這個只有在大阪商人之間流通的字彙,不難理解在她心裡仍儘可能地希望保留舊社會流傳下來的秩序。另一個例子則是,當幸子要外出參加音樂會時,希望有人幫她打理身邊周遭時,會喊「□□□□、□□□。」。不難看得出來「□□□□」這個在大阪商人之間原本用來指稱小女兒的特殊字彙,在這個家裡仍是相當常見。如同前面所述,蘆屋從江戶時代起就深受古老大阪文化的影響。所以在日常生活裡會使用「御寮人樣」或是「□□□□」之類的語詞,並不特別。但是,這個習慣在搬遷到東京的本家裡,應該會漸漸消失不見。從去過東京的雪子口中可以得知,在東京這邊就算說出「蒔岡」的名號,也沒有任何人知道他們,於是鶴子夫婦兩人□開不必要的排場,過著樸實儉約的生活。在東京的人際往來之中,沒有人會先特地去練得一手好字,再來開始寫感謝信,一是沒有這個閒暇,二是沒有這個必要性。相較之下,「蒔岡」這塊招牌的名與實,反而對蘆屋這個「分枝」而言,均不可或缺。值得注意的是,同住一個屋簷下的妙子會用「御寮人□□」來稱呼幸子,「御寮人□□」這個詞在不知不覺當中,具有填補「蒔岡」家這塊招牌的功用。妙子的性格就如同美容院老闆娘曾經說過,她就像是現今二十多歲的年輕太太一樣,是一位「頭腦好的非常多」的人,深知如何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完成家事,並且具有行動力的新世代。話雖如此,妙子對船場地區的感情或許會與幸子、雪子兩人有所不同,但在作品裡可看見她亦會無意識地使用「御寮人□□」一詞。
此時,若我們把閱讀的焦點切換到日語原文上面,必須注意在作品裡同樣是「御寮人樣」一詞,會因為說話者而有不同的寫法。雖然這個字在日文發音上都是「□□□□□□」,書寫成文字時則有「御寮人□□」及「御寮人樣」兩種方式。如同前述,前者出現在當妙子對著女僕稱呼幸子的場面。後者則出現在昔日於蒔岡家擔任僕人的兒子,面對幸子指稱位於東京的長女鶴子的場面。後者的情況中,由於是僕人稱呼本家的太太之故,會使用「御寮人樣」是極為自然的選擇結果。而妙子跟幸子為親屬關係,且又住在同一個屋簷下,兩人之間沒有什麼拘束感,所以稱呼幸子時不是使用「樣」,而是以「□□」來表示。文章內如果妙子是以「御寮人樣」稱呼幸子時,則會給讀者過度誇張、不自然的感覺,且彰顯兩人之間的心理距離。在這裡我想要強調的是,上述細微的語感差異在中文裡使用表示女主人的「太太」一詞並不能完全含括,而唯有藉著在表示方法上有較多選擇的日文才能傳達出來。從漢字與平假名的組合之下,微妙的使用方法暗示著人與人之間的上下關係,或是感情心理上的遠近距離。還有,作家谷崎潤一郎是在當時(甚至是現今為止)特別意識到日文具有此一特徵的作家。
實際上,谷崎在開始書寫《細雪》之前,曾經收集過出現在日文小說裡各式人物階層所使用的詞彙,加以考察之後,於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出版《文章讀本》一書。這本書已由□明珠女士翻譯完成,透過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谷崎在《細雪》之前,於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發表了《貓與庄造與兩個女人》,這部作品以蘆屋靠近海邊的地區為舞臺,內容以描寫當時的庶民生活為主。中文版同樣也是由□明珠女士翻譯,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
谷崎曾在〈私的貧乏物語〉的散文當中寫道,隨著年華老去,當自己無法再像年少時期一樣藉由空想,以大膽、莽撞的方式進行創作時,「唯有倚賴事實或經驗,創作的熱情才能傾瀉而出」。從這段文章看來,我們不可否認當他創作《細雪》的時候,昭和十年(一九三五)起與森田松子正式婚姻生活裡的「事實或經驗」提供給他質量豐富的創作題材。小說裡谷崎對蒔岡一家的基本構成、姐妹的特徵、擁有閒暇時間夫人們的生活,或是賞櫻、捕流螢等代表四季的日常活動做出詳盡的描寫。谷崎雖住在距離蘆屋不遠之處,但他未曾在蘆屋居住過。然而,《細雪》裡的世界並不是由谷崎用空想所建構出來的,而是谷崎自己多次造訪蘆屋之後,最後決定把蘆屋作為小說的舞臺,這也同時意謂著《細雪》並未跳脫出谷崎本身的實際「生活範圍」。不過,《貓與庄造與兩個女人》裡阪神鐵路上靠近海邊的蘆屋,以及《細雪》裡阪急蘆屋川車站附近的蘆屋,帶給讀者兩種截然不同的城市印象。雖說現實生活裡的蘆屋也是如此,而在《細雪》裡谷崎更是為它披上一層華麗的薄紗。與蘆屋相鄰的神戶市魚崎地區裡有一座名為倚松庵的古屋,這裡曾是谷崎的故居,倚松庵現今被留存下來並對外開放供世人參觀。至少現在看來,倚松庵的規模跟《細雪》裡對蘆屋的描述還有一段差距。谷崎會做出比現實生活更加華麗的描寫,應該就如同一般認為,谷崎創作本作品之前,花費三年歲月才告完成的《源氏物語》白話文翻譯工作,對他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細雪》部份內容曾分為兩次於雜誌上發表,由於軍方干涉之故而無法繼續登載下去。儘管如此,谷崎仍於戰亂中孜孜不倦地書寫這部作品,並在戰爭結束後於昭和廿二年(一九四七)至廿三年(一九四八)年之間透過雜誌發表下冊內容,整部作品的全貌才得以逐漸完整,並劃下完美句點。這部誕生於日本瀕臨國家興亡關頭的文學結晶,不難想像在其背後隱藏著戰後日本人忍受飢餓貧困與戰禍之苦,對富貴生活投以欣羨的目光,以及面對失去戰前曾經擁有的優雅生活之際,所抱持著強烈的哀傷心情。
最後,我還想補充一點:「細雪」這個詞彙有雪花輕飄飛舞的意思,這並不是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詞彙,而是具有詩情意境的文言雅詞。
專修大學教授山口政幸∕文鄧延桓∕譯
一「阿妙,拜託啦!──」從鏡中一看到從走廊到背後來的妙子,就把自己正在塗頸子的刷子遞給她,也不看她那邊,注視著映在眼前穿和服長襯衫姿態,露出後頸的臉,彷彿他人的臉般凝視著。「雪子在下邊做什麼呢?」幸子問。「大概在看悅子彈鋼琴。」──原來樓下傳出練習曲的鋼琴聲音,顯然是雪子先裝扮好的當兒被悅子逮到,要雪子去看她練習吧!悅子是即使媽媽外出時只要有雪子在家就會乖乖看家的小孩;可是今天母親和雪子、妙子三個人都要出門,所以心情有一點不好,不過說好二時開始的演奏會一結束雪子先走一步,會在晚飯之前趕會回來,這樣子悅子總算可以接受。「耶,妙子,雪子的親事,還有一樁哪!」「哦──」妙子從姊姊的後頸子到兩肩,留下鮮明的刷痕再敷上白粉。幸子絕不是水蛇腰;不過肌膚豐腴,從稍稍隆起的雙肩到背部,秋天的陽光照在嫩滑的肌膚表面呈現的光澤,不像已過了三十歲的人,看來很有彈性。「是井谷太太提的婚事呀─—」「哦──」「是薪水階級啊,聽說是MB化學工業公司的職員。」「拿多少薪水呢?」「月薪一百七八十圓,加上獎金大概二百五十圓上下吧!」「MB化學工業,是法國系統的公司吧?」「是呀——妙子倒是很清楚哪!」「當然知道,這種小事。」這樣的事年紀最小的妙子,比兩個姊姊的任何一個都清楚。妙子對意外的不懂人情世故的姊姊們,在這方面多少看扁她們,說話的口吻倒像自己是年長者。「那公司的名字,我聽過。─—總公司在巴黎,是資本額很大的公司哪!」「在日本,神戶的海岸路上不是有一棟大樓嗎?」「是嘛,在那裡上班啊。」「他會說法語嗎?」「嗯!大阪外語大法文系畢業,也在巴黎住過短暫的時日。除了上班,還當夜校的法文老師,薪水大約百圓左右,兩邊加起來有三百五十圓。」「財產呢?」「沒什麼財產。鄉下有母親一個人,有她住的從前的老房子,和自己住的六甲的房子跟土地。─—六甲那邊是分期付款買的小小的住宅。不值什麼錢哪!」「即使這樣也可以省掉房租,可以過四百圓以上的生活啦!」
 熊出沒之探險日記·超好玩的故事拼圖...
熊出沒之探險日記·超好玩的故事拼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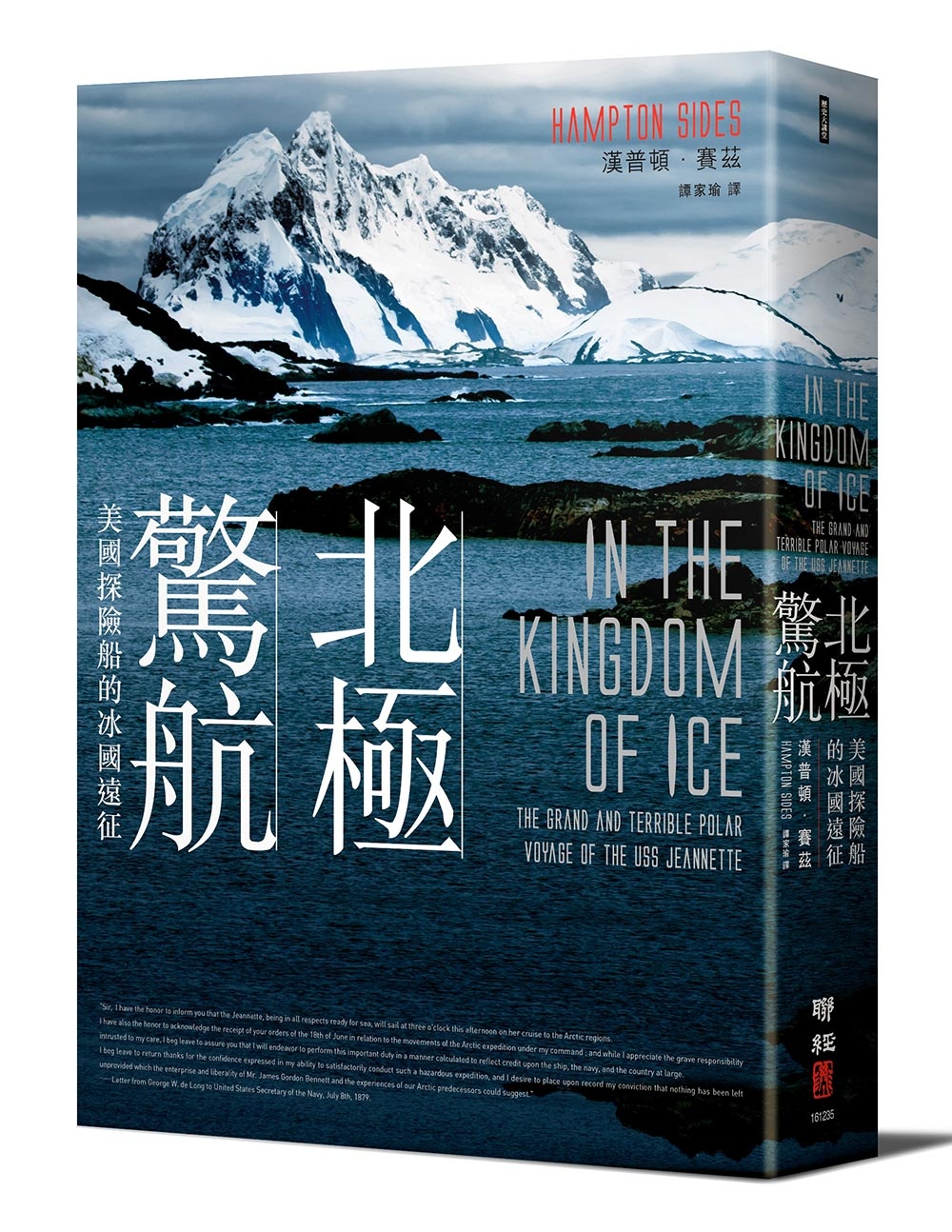 北極驚航:美國探險船的冰國遠征
北極驚航:美國探險船的冰國遠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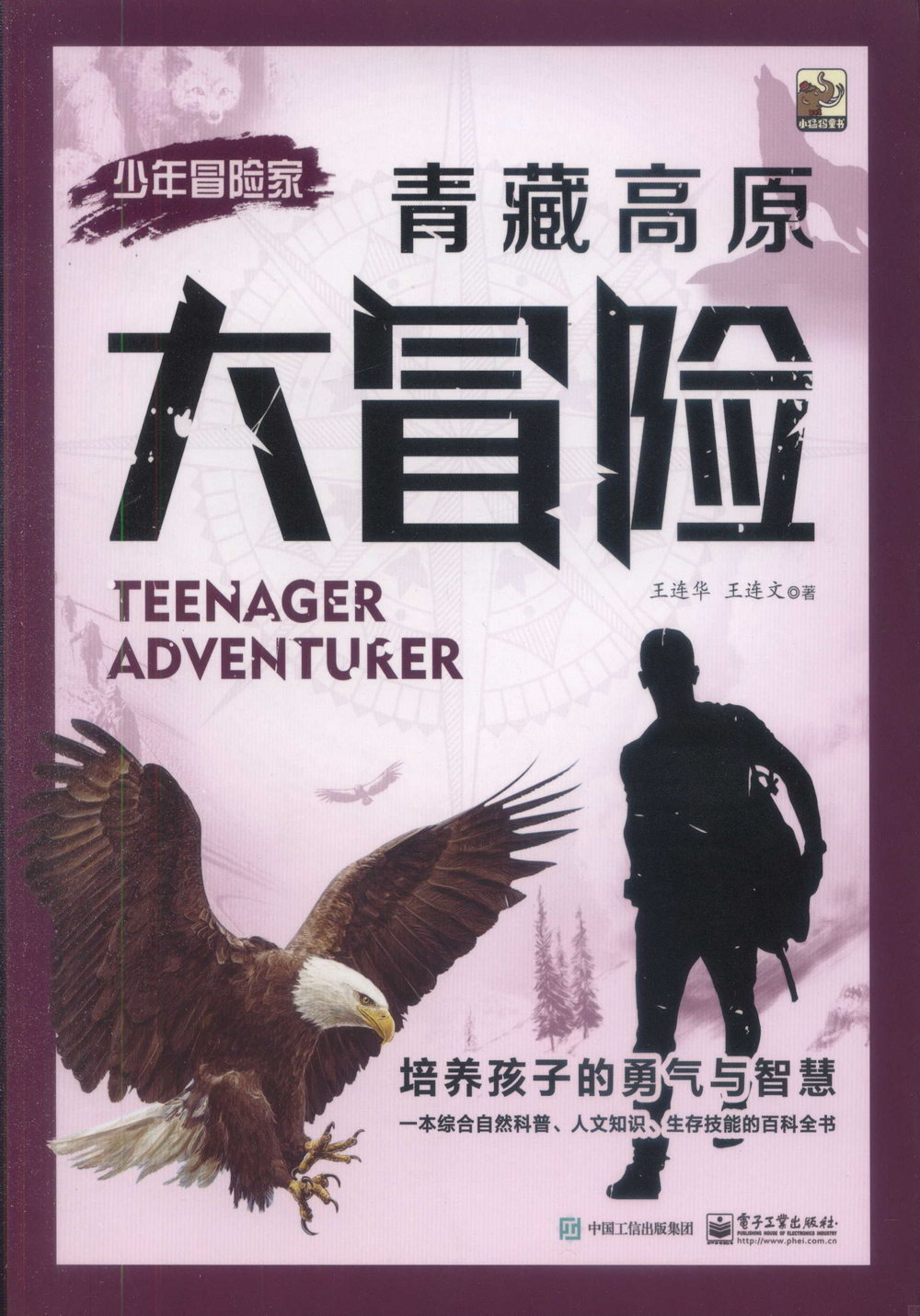 青藏高原大冒險
青藏高原大冒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