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史綱(青少年普及版) | 生病了怎麼辦 - 2024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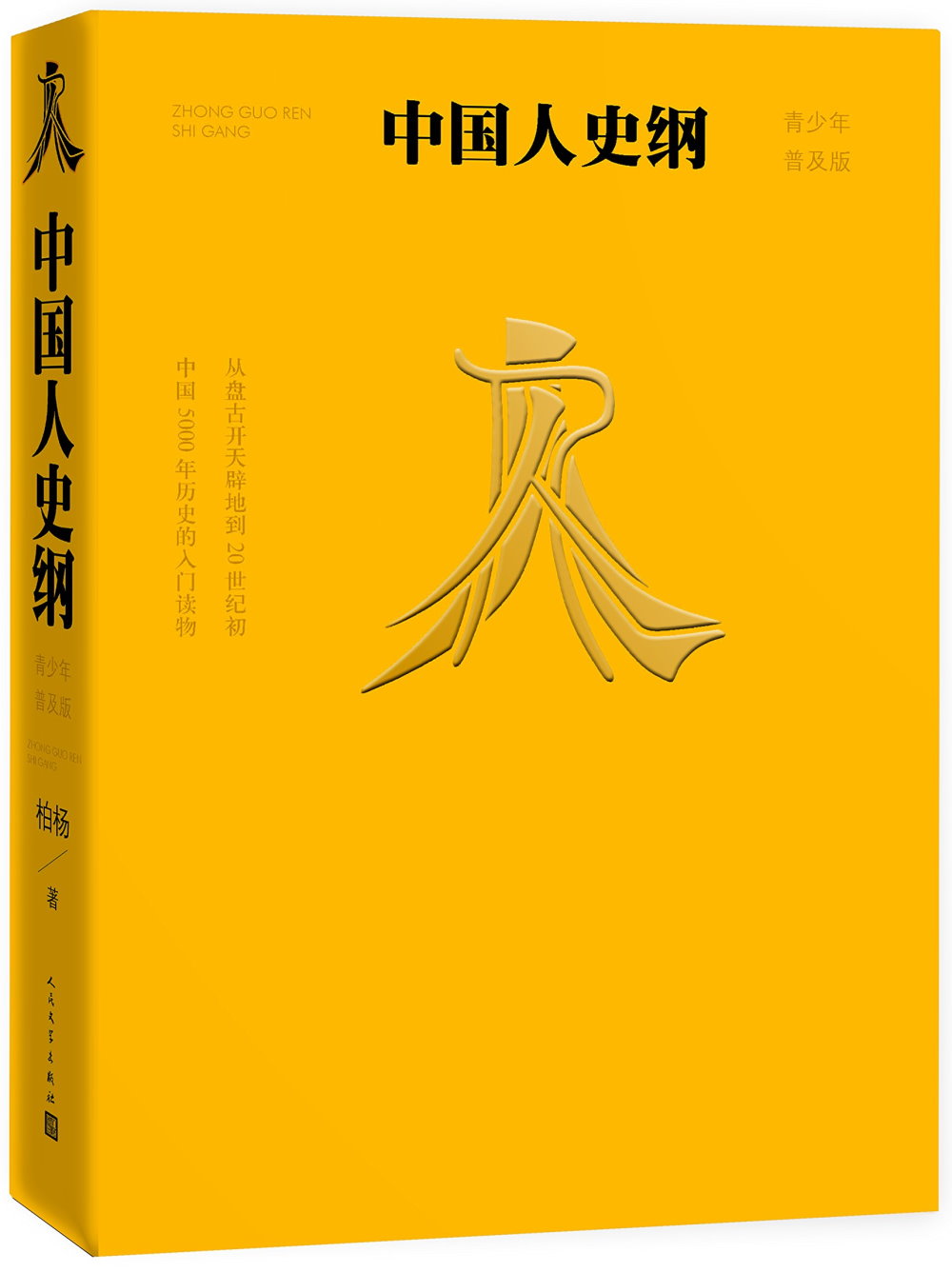
中國人史綱(青少年普及版)
柏楊的史學代表作。它以時間為經,從盤占開天闢地一直寫到20世紀初;以事件為緯,內容涵蓋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此書篇幅浩大、結構清晰、文字流暢,自面世以來,深受讀者歡迎,不斷再版,是學習中國通史的首選讀物。為方便學齡期讀者閱讀,特推出此版本。
讀柏楊著作常常讓我想到魯迅(代序)錢理群/1
序/9
第1章 歷史舞臺
一空中·馬上/2
二河流—湖泊/5
三山/10
四沙漠·萬里長城/12
五城市/15
六地理區域/1
七演員/25
第2章 神話時代
一盤古與三皇——中國的創世紀/32
二五氏/34
東西方世界/37
第3章 傳說時代
一黃帝王朝/40
二唐堯與虞舜/46
東西方世界/49
第4章 半信史時代
一夏(前2205—前1766)/53
二商(前1766前1122)/59
三西周王朝(前1122—前771)/62
東西方世界/70
第5章 春秋戰國時代(前770—前256)
一春秋早期/75
二春秋晚期/90
三戰同時代/106
東西方世界/128
第6章 秦漢時期(前221—220)(上)
一大一統的秦帝國(前221—前207)/133
二曇花一現的西楚王國(前206—前202)/146
三西漢王朝(前201—9)/149
東西方世界/172
第7章 秦漢時期(前221—220)(下)
一新王朝(8—23)/176
二短命的玄漢政權(23—25)/180
三東漢時期(25—220)/181
東西方世界/199
第8章 三國時代(220—280)
一三個政權的命運/204
二政制、九品、清談/206
三三國時代的迅速結束/208
東西方世界/209
第9章 兩晉時期(265—420)
一腐朽的西晉與自殘的八王之亂/212
二大分裂時代開始/218
三偏安一隅的東晉王朝/226
四北中國的大混戰/227
五前秦帝國與東晉王朝的對峙/230
六淝水戰役——歷史的命運/232
七前秦帝國崩潰北中國再陷混戰/236
八東晉及短命王國的相繼滅亡/242
東西方世界/244
第10章 南北朝時期(420—589)
一南中國的朝代更迭與混戰/250
二南中國的統一努力/260
三北中國的政權更迭與混戰/263
四南北朝的政治特點及文化發展/275
東西方世界/279
第11章 隋朝(581—618)
一楊堅的內政外交/282
二仁壽宮弑父凶案/284
三楊廣的大頭症/286
四改朝換代的混戰/290
東西方世界/291
第12章 萬國衣冠拜冕旒——唐朝(618—907)
一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294
二唐代社會文化/297
三中國疆土的再擴張/303
四武瞾的南周/309
五開元盛世/313
六唐朝走上了下坡路/318
七唐王朝的盡頭/323
東西方世界/331
第13章 五代十一國的小分裂時代(907—979)
一大分裂的開始/334
二短命政權間的殊死戰/336
三宋帝國統一中國本部/345
東西方世界/345
第14章 宋王朝(960—1279)(上)
一杯酒釋兵權/349
二新興宋王朝的外交形勢/349
三宋朝的政治/355
四宋朝的文化/363
五錯綜的四國關係及彼此消長/367
六開封陷落及二帝被擄/373
東西方世界/375
……
第15章 宋王朝(960—1279)(下)
第16章 元(1206—1368)
第17章 明( 1368—1644)
第18章 大清帝國( 1616—1911)
附錄 延伸閱讀/545
第17章 明(1368—1644)
讀柏楊著作常常讓我想到魯迅(代序)
錢理群
剛才看了柏楊先生講話的錄像,我很感動。特別是他最後講的那句話:一個人在鋼刀架在脖子上的時候,能不能堅持說真話,這才是一個真正的考驗,經過了這樣的考驗,才能對他蓋棺論定。這句話很有震撼力,裡面有一種精神,我以為就是與魯迅先生相通的硬骨頭精神。
我在讀柏楊先生著作的時候,也很自然地要聯想起魯迅先生。我拿到這本柏楊先生的《中國人史綱》,就想到魯迅曾經有過的一個寫作計畫。魯迅在《晨涼漫記》這篇文章裡,說到他想選擇“歷來極其特別,而其實是代表著中國人性質之一種的人物,作一部中國的‘人史’。”並且已經有一些初步的構想:“惟須好壞俱有,有齧雪苦節的蘇武,捨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後已的王莽,有半真半取笑的變法的王安石;張獻忠當然也在內。”但魯迅最後說:“現在是毫沒有動筆的意思了”。在我看來,柏楊先生的《醜陋的中國人》和《中國人史綱》,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魯迅所期待的這樣的“中國人史”。在這裡,我感覺到柏楊先生和魯迅先生在精神追求上的某些相通,至少有兩點是相通的。
第一是兩個堅持:堅持對中國國民弱點的批判,堅持對中國傳統文化弱點的批判。這兩個批判顯示的是一種啟蒙主義的立場。這樣一個立場,恰好反映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時代精神,柏楊先生的《醜陋的中國人》就是在那個年代傳到大陸,產生了巨大影響的。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柏楊先生的著作影響了八十年代的一代人,培育了一代人。當然,到了九十年代,我們,也包括我自己在內,對啟蒙主義是有所反省的,主要是過分誇大了啟蒙的作用,以為只要人的思想變了,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而九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一世紀初,我們所面臨的現實,卻一再讓我們感到啟蒙的無力,制度的改造、變革與建設的重要與迫切。這樣的覺悟本來是意味著我們對中國問題認識的深化,是件好事。但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知識份子,總喜歡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這背後就有一個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於是,就有人著意將思想啟蒙和制度變革與建設對立起來,宣揚“制度萬能”,這其實與“啟蒙萬能”在思維方式上是完全一致的。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究竟應該怎樣看待思想啟蒙與制度變革、建設的關係?在我看來,它們分別抓住了中國的兩個要害,是不可或缺的,因而是可以而且應該互為補充,互相促進的。
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說,思想啟蒙與制度變革、建設,都各有其價值,又各有其局限,甚至存在著某種陷阱,無限誇大自己的價值,沒有“邊界意識”,就有可能走向反面。我們已經談到了缺乏制度變革、建設支撐的思想啟蒙的無力,反過來,不注意人的思想變革的制度變革也是無用的,因為制度是要靠人去建設與實行的,就如魯迅所說,中國是個“大染缸”,中國人心不變,習性不變,再好的制度引進中國,也是要變質的。而且在具體實踐中作怎樣的選擇,是做思想啟蒙工作,還是制度變革、建設工作,也要取決於每一個知識份子個體的主客觀的條件,比如說,我這樣的普通的大學教師,或者柏楊先生這樣的學者,大概只能做思想啟蒙工作,即使思想上更重視制度建設,我們也只能鼓吹,而鼓吹其實也只是啟蒙。當然,在做啟蒙工作時,應該有一個自我警戒,就是要看到自己的局限,由此形成一個立場:“既堅持啟蒙,又質疑啟蒙”。有了這樣的立場,我們對柏楊先生的《醜陋的中國人》、《中國人史綱》這樣的著重啟蒙的著作,就可能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它是有價值的,是有利於中國思想文化的改造與建設,中國人心的改造與建設的,同時又是有限的。
但我擔心,這樣的有限的作用,在當下的中國大陸,也是很難發揮的。——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天的中國,已非八十年代的中國了。特別是現在的大陸思想文化界充斥著一種否定,甚至詆毀啟蒙主義的思潮。有的人已經走到了這樣的極端:把啟蒙主義與專制主義等同起來,把五四思想啟蒙運動視為文化大革命的先聲,魯迅這樣的既堅持啟蒙主義、又質疑啟蒙主義的思想家更是被判決為專制主義的同謀,以至罪魁禍首。值得注意的是,對啟蒙主義的討伐,除了有著前述“制度萬能”的理念外,還有兩個旗號,一是“寬容”,一是“建設”。本來,就其原意而言,“寬容”與“建設”是兩個很好的概念,是一個健全的社會所必須的;但在中國現實語境下,在某些人的闡釋裡,這樣的“寬容”與“建設”是與啟蒙主義的批判精神對立的,就是說,如果你要像魯迅與柏楊先生那樣堅持兩個批判:批判中國國民性的弱點,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弱點,你就是不寬容,缺乏建設精神,就應該對你不寬容。而且還有一個可怕的罪名在等著你:你是破壞民族文化的千古罪人。
坦白地說,我一邊讀柏楊先生的這部《中國人史綱》,一邊為他捏一把汗,因為他在這本書裡,重點批判了兩個東西,一個是中國帝王所代表的專制主義,一個是某些儒生所代表的專制體制的奴才與幫閒、幫兇。其實這也是魯迅批判的重點。而帝王和儒生是當下中國最需要的兩個群體,是批判不得的。在一片歌頌“太平盛世”的世紀狂歡裡,無論在電視,還是出版物裡,這些帝王、儒生都成了“香餑餑”,成了追逐的“明星”。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引入柏楊先生的《中國人史綱》,至少是不合時宜的,弄不好,柏楊先生也會被某些人視為“破壞民族文化的千古罪人”。不過就我個人而言,大概因為自己早就是不合時宜的人,因此讀這本《中國人史綱》,卻能引起很多的共鳴。特別是滲透全書的民族自省精神——這也是我感覺到的柏楊先生與魯迅精神相通的第二個方面,它引起了我的許多聯想。
當下最流行的一句話:以史為鑒。這當然是一個對待歷史的重要原則,柏楊先生的《中國人史綱》就是一部“以史為鑒”的著作。但在有些人的闡釋裡,以史為鑒是專對外國人講的,那麼,我們中國人要不要也以史為鑒?批判別人篡改歷史,這當然很對,很有必要,但我們自己對歷史的態度又怎麼樣?好像沒有人談,這裡所缺少的正是一種民族自我反省的精神。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時,“歌頌”我們的勝利,“控訴”侵略者的罪惡成了主旋律。作為普通老百姓沉湎于民族自豪感的情緒發洩,這或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為知識份子,是不是應該與這樣的氣氛保持一點距離,應該有點理性的思考,有一點冷靜的反思、反省:這本應是知識份子的職責所在。記得在五卅運動中魯迅就提醒年輕的學生:“對於群眾,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啟發明白的理性”,如果聽任民眾非理性的公憤氾濫,“歷史指示過我們,遭殃的不是什麼敵手而是自己的同胞與子孫”(《雜憶》)。
但我們老是沒有記性,總是忘記歷史的教訓,也就是口喊“以史為鑒”,實際不以史為鑒。在慶祝勝利的狂歡裡,有的知識份子比民眾還要狂,歡得厲害,根本忘記了引導民族反省的職責。記得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我說了一句不合時宜的話,我說校慶應該是學校自我反省的日子,結果引起軒然大波。現在在全民慶祝勝利的時候,重提民族自省,大概就更不合時宜了。這裡有一個如何對待民族情緒的問題。魯迅在五卅運動中就討論過所謂“民氣”。他說,一味鼓動“民氣”而不注重增強“民力”,“國家終亦漸弱”,“增長國民的實力”,這才是真正的維護民族利益之道(《忽然想到十》)。一個民族不能沒有“氣”,但必須在其中注入理性精神;一個民族不能沒有自豪感,但更要有自省精神,其實,敢於、善於自我反省,正是真正的民族自信心的表現,是一個民族是否成熟的重要標誌。知識份子應體現並努力促進民族的成熟,而不是相反。
我看柏楊先生的著作,最感興趣的是他對甲午戰爭的反省。這是中日之間第一次遭遇,我們失敗了。八年抗戰,我們是“完全勝利”了。據說這是“用血肉之軀”換來的勝利,勝得相當悲壯,所以曾有過“慘勝”之說。因此在歡慶勝利以後,還得想一想,這不得不以血肉之軀來取得勝利的原因是什麼?我們能不能老是以血肉之軀來取得勝利?說句不吉利的掃興的話,如果不認真總結、吸取教訓,恐怕有一天我們還得用血肉之軀來抵禦侵略,那就太可怕了。柏楊先生把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兩條,一個是科舉制度,一個是貪污腐敗。但是我很奇怪,科舉制度現在也成“香餑餑”了。好些文章大講科舉制度如何如何好,據說西方的文官考試制度就是從中國學來的,而且據說正是廢除了科舉制度,才導致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斷裂(?),因此我們現在要回到科舉制度那裡去,云云。
我不反對對科舉制度作學理的研究,對其作出更科學、全面的評價,但我奇怪的是,為什麼總要回避在中國歷史上的科舉制度與封建專制體制的密切聯繫這樣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而且事實上我們現在也還有新的科舉制度,在我看來,我們的評職稱、評什麼什麼點,就是科舉制度“請君入 ”那一套,這給我們帶來了什麼?大家都是清楚的。科舉制度成了寶貝,這大概是柏楊先生絕對想不到的。還有腐敗,腐敗為什麼屢禁不止?這個問題不好回答。大家都在談中國腐敗問題,但是很少人探討背後的原因。柏楊先生要追根問底,也是不合時宜。
今天早上我讀到胡風先生的一段話,講抗戰時期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潮,胡風作了這樣的概括:“只准許歌頌勝利,只准許歌頌中國文化又古又好,中國人又自由又幸福。只准許對敵人的弱點和沒有出路加以嗤笑,聊快一時的人心”。如果這個時候,有人像魯迅一樣跳出來說要講啟蒙主義,要反省我們自己,會是什麼樣一種情況?胡風因此設想了一個問題:如果魯迅活到了抗戰時期,他會怎麼樣?——這個“魯迅活在現在他會有怎樣的命運?”這是一個在魯迅逝世以後,一直纏繞著中國知識份子的問題,在不同歷史時期都會不斷地提出,在1948年、1957年都提出過,前兩年又引起熱烈討論。而1941年胡風的回答卻是相當嚴峻:“如果真的他還活著,恐怕有人要把他當作漢奸看待的”(《如果現在他活著》)。
坦白地說,我讀了胡風的這篇文章,是非常震撼的。我實在弄不明白,我們在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時候,我們的文化思潮為什麼還和六十四年前的抗戰時期的1941年一模一樣,連用詞都差不多,還是只准歌頌,只准說敵人壞話,不能反省自己?而且還真有人把魯迅“當作漢奸看待”,前不久我就在網上看到過這樣的義正詞嚴的討伐“漢奸魯迅”的文章,我特別感到痛心的是,據說文章的作者是一個年輕人。那麼,是什麼樣的思想文化在引導著我們的年輕一代,這將導致什麼後果呢?我由此想到,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引入柏楊先生的帶有鮮明的反省民族文化傾向的著作,他又會有什麼樣的遭遇呢?會不會也被某些人,包括某些年輕人,當作漢奸看待呢?想到這裡,我真有些不寒而慄。
但好在中國人口多,地方大,而且一種思潮壟斷一切的時代已經過去。因此,柏楊先生的著作這次再度引入大陸,雖然已不可能像上一世紀的八十年代那樣引起轟動,但也總能尋得知音,產生影響。因此,我一面擔心柏楊先生的著作和當下中國大陸思想文化主流的東西相違背,是不和諧的聲音,但同時又想,這可能正是柏楊先生作品的價值所在:我們正需要這樣的聲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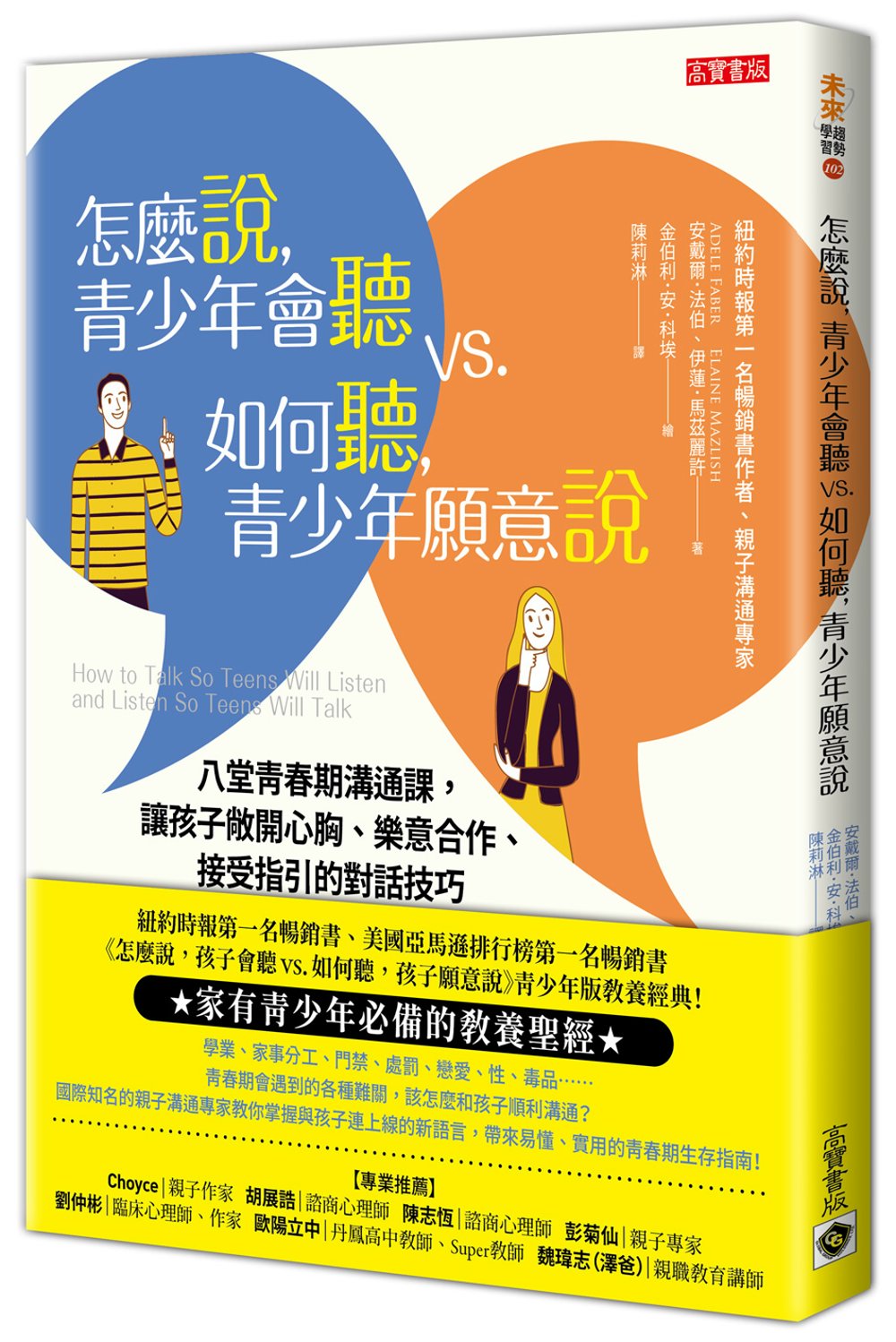 怎麼說,青少年會聽vs.如何聽,青...
怎麼說,青少年會聽vs.如何聽,青... 哮喘
哮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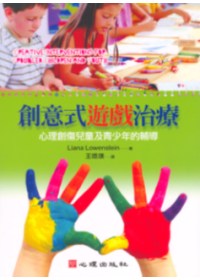 創意式遊戲治療-心理創傷兒童及青少...
創意式遊戲治療-心理創傷兒童及青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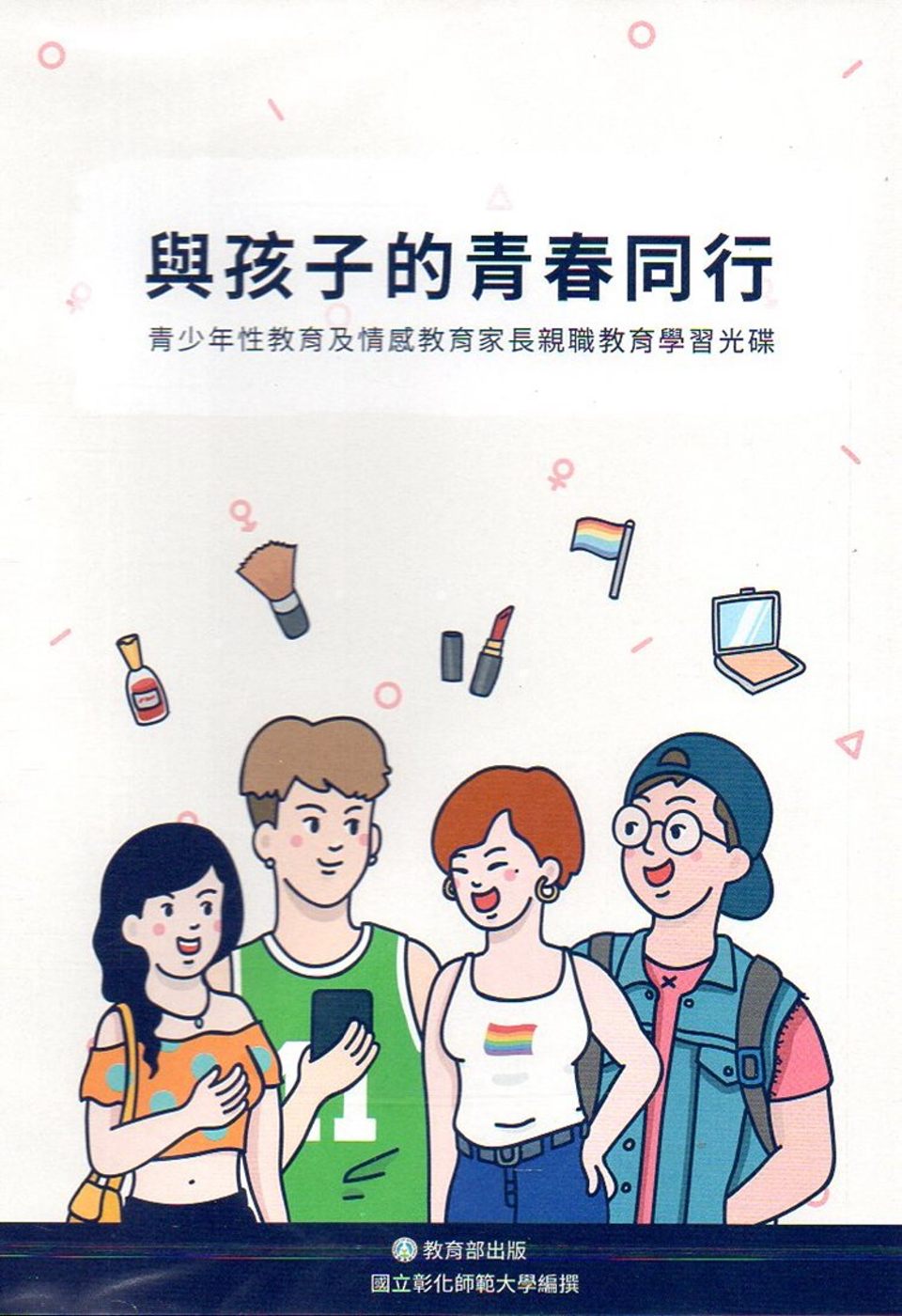 與孩子的青春同行:青少年性教育及情...
與孩子的青春同行:青少年性教育及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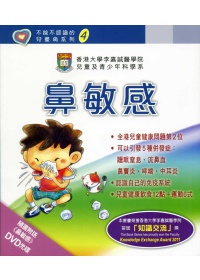 鼻敏感
鼻敏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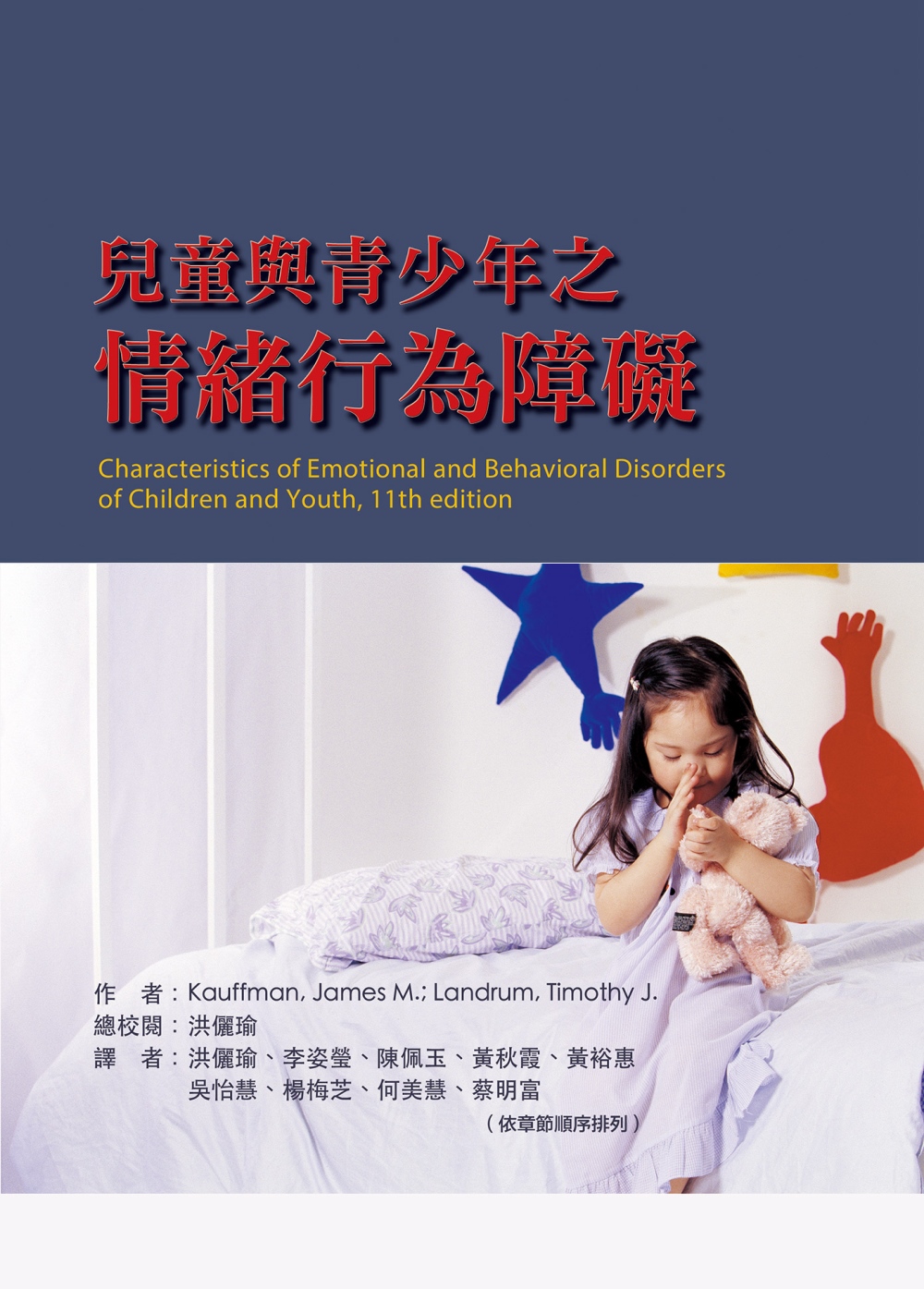 兒童與青少年之情緒及行為障礙(二版)
兒童與青少年之情緒及行為障礙(二版) 建立社會關係及互動技巧:教導自閉症...
建立社會關係及互動技巧:教導自閉症... 亞斯柏格症兒童及青少年:社會技能訓練
亞斯柏格症兒童及青少年:社會技能訓練 解構青少年犯罪—香港、新加坡和上海...
解構青少年犯罪—香港、新加坡和上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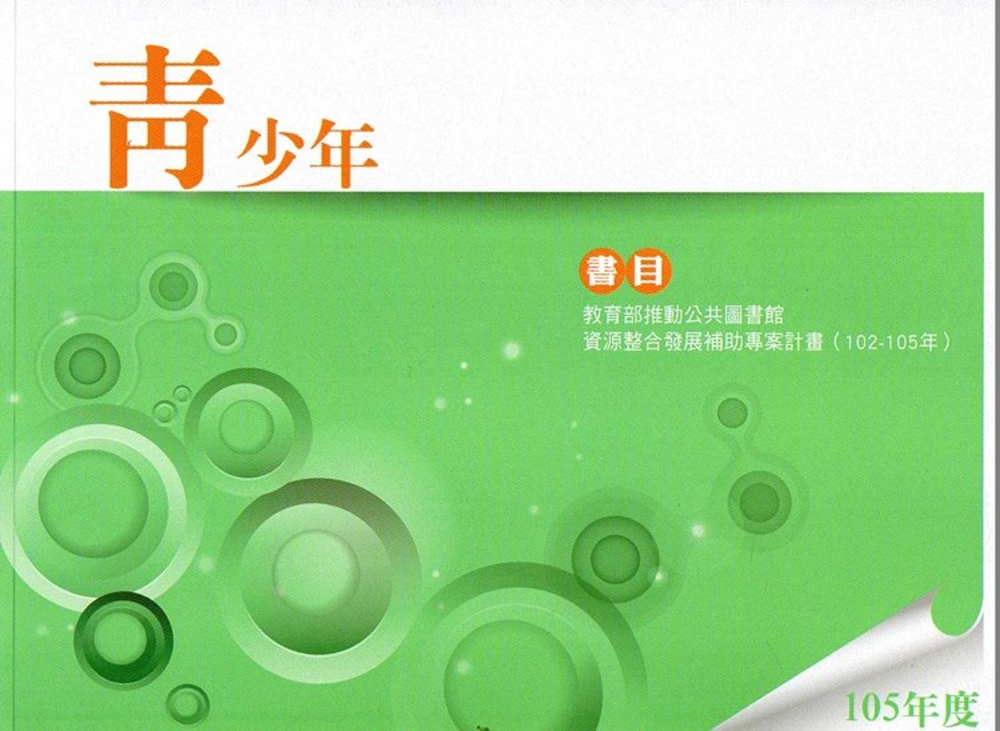 105年度青少年書目
105年度青少年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