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旅書札:一位女士在洛磯山脈的生涯 | 生病了怎麼辦 - 2024年11月

山旅書札:一位女士在洛磯山脈的生涯
伊莎貝拉‧璐西‧博兒,一八三一年出生,一位牧師的女兒。一八七二年她依照醫生叮囑,獨自赴澳洲旅行,期盼受困於背脊痛和神精衰弱的病體能有起色;沒想到,自此她卻展開了持續一輩子的冒險旅行生涯。 一八七三年秋天,這位四十二歲的英國女性從舊金山東岸搭火車出發,前往位於內華達山脈的加州特拉基;之後,她騎上一匹高大灰馬,穿著夏威夷騎裝,從加州旅行到科羅拉多州的洛磯山脈,並在美麗絕倫、與世隔絕的埃絲蒂斯公園度過一段難忘時日,最後更在氣候惡劣的嚴寒冬日,騎著精神抖擻的半馴化馬「鳥兒」,隻身探索這片「蠻荒西部」。在這段維時三個多月的旅行期間,她旅居農莊和採礦營,幫忙清潔、煮食,學會了駕駛馬車以及驅趕牛隻,並在亡命徒「山中的吉姆」的協助下,攀上標高四千四百八十公尺的長峰頂峰──這趟頗具挑戰性的旅程,幾乎耗盡博兒的全副精力。 當時她停留最久的科羅拉多,還是個不屬於美國合眾國的未開發地區,它的法律與鐵路都尚在整建中,居住於此的是生活簡陋、狂飲無度的拓荒者,他們剛由印第安人手中奪過這塊土地。伊莎貝拉的勇氣與毅力傳遍了當地屯墾區,以致當她詢問是否可以穿越積雪咫尺的小徑探訪綠湖時,驛站守衛回答:「如果是那個在山中旅行的英國女子,我們可以給她一匹馬,其他人不行。」 伊莎貝拉在這些寫給摯愛小妹涵蕊雅塔的信中,道出了她的一切遭遇。儘管這些書信寫於一百多年前,我們仍能分享伊莎貝拉眼中的洛磯山,那裡有未受人工雕琢或人為破壞的壯麗景色、豐富的野生動植物、破落山居、偏遠拓荒小鎮……。透過這些書信,我們的眼前浮現了她和響尾蛇、野狼、美洲獅、大灰熊面對面遭遇的情景,心中升起了她一覺醒來身上覆滿白雪的奇異感受,腦中也分享了她對採礦人和拓荒者快活性格的觀感。 「伊莎貝拉‧博兒是位完美的旅行者,還沒有人有過像博兒小姐那樣的歷險。」──《觀察家》(Spectator)雜誌 「一趟驚人的旅行,一本無可比擬的旅行書札。」──德夫拉‧穆菲(Dervla Murphy),《愛爾蘭時報》 作者簡介 作者:伊莎貝拉.璐西.博兒 作者簡介:Isabella Lucy Bird, 1831-1904 一位牧師的女兒,生長於英國西部赤夏郡(Cheshire)泰藤霍爾鎮(Tattenhall)。青少年的她一直受脊背病痛折磨,一八五四年依照醫生叮囑赴美加地區旅行,以改善健康狀況。一八六○年,父親去世,伊莎貝拉與母親及妹妹涵蕊雅塔(Henrietta)遷居愛丁堡。她繼續承受脊背病痛、失眠和沮喪等症的困擾,直到四十歲她前往澳洲旅行,繼而造訪夏威夷時,她的健康奇蹟似地有了進步。她寫下《三明治島六月記》,並且登上了世界最雄偉的火山毛納洛亞。一八七三年,伊莎貝拉出發到洛磯山旅行;她這些描述洛磯山風光的書信於一八七九年集結成這本《山旅書札》。在家停留了一段時間之後,她又再度出發旅行,這次是到日本北部的北海道及馬來半島的土著區。這兩次旅行的結果,她完成了《日本無可比擬的徑道》和《金色的半島居民》。一八八一年,博兒與約翰.畢夏普(John Bishop)醫生成婚。他於一八八六年去世,三年後,伊莎貝拉再度出發到西藏西部、拉達克、伊朗沙漠、庫德斯坦高地、朝鮮半島,以及中國內陸等偏遠地區旅行。這些不尋常的探險旅程記載在《伊朗及庫德斯坦之旅》、《在西藏人中》、《朝鮮及其鄰邦》,以及《揚子江河谷及其他》。伊莎貝拉於一八九八年從遠東回到愛丁堡;七十歲那年,她完成了最後一次的旅行,騎著蘇丹王送她的一匹黑牡馬造訪摩洛哥。一九○四年,她在家中安祥辭世。
編輯前言
詹宏志
探險家的事業
探險家的事業並不是從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才開始的,至少,早在哥倫布向西航行一千多年前,中國的大探險家法顯(319-414)就已經完成了一項轟轟烈烈的壯舉,書上記載說:「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編按:指今日的中印度),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法顯旅行中所克服的困難並不比後代探險家稍有遜色,我們看他留下的「度沙河」(穿越戈壁沙漠)記錄說:「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這個記載,又與一千五百年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穿越戈壁的記錄何其相似?從法顯,到玄奘,再到鄭和,探險旅行的大行動,本來中國人是不遑多讓的。
有意思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探險旅行,多半是帶回知識與文化,改變了「自己」;但近代西方探險旅行卻是輸出了殖民和帝國,改變了「別人」。(中國歷史不能說沒有這樣的例子,也許班超的「武裝使節團」就是一路結盟一路打,霸權行徑近乎近代的帝國主義。)何以中西探險文化態度有此根本差異,應該是旅行史上一個有趣的題目。
哥倫布以降的近代探險旅行(所謂的「大發現」),是「強國」的事業,華人不與焉。使得一個對世界知識高速進步的時代,我們瞠乎其後;過去幾百年間,西方探險英雄行走八方,留下的「探險文獻」波瀾壯闊,我們徒然在這個「大行動」裡,成了靜態的「被觀看者」,無力起而觀看別人。又因為這「被觀看」的地位,讓我們在閱讀那些「發現者」的描述文章時,並不完全感到舒適(他們所說的蠻荒,有時就是我們的家鄉);現在,通過知識家的解構努力,我們終於知道使我們不舒適的其中一個解釋,就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說的「東方幻想」(Orientalism)。這可能是過去百年來,中文世界對「西方探險經典」譯介工作並不熱衷的原因吧?或者是因為透過異文化的眼睛,我們也看到頹唐的自己,情何以堪吧?
編輯人的志業
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探險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大內容;不了解近兩百年的探險經典,就不容易體會西方文化中闖入、突破、征服的內在特質。而近兩百年的探險行動,也的確是人類活動中最精彩、最富戲劇性的一幕;當旅行被逼到極限時,許多人的能力、品性,都將以另種方式呈現,那個時候,我們也才知道,人的鄙下和高貴可以伸展到什麼地步。
西方的旅行文學也不只是穿破、征服這一條路線,另一個在異文化觀照下逐步認識自己的「旅行文學」傳統,也是使我們值得重新認識西方旅行文學的理由。也許可以從金雷克(Alexander W. Kinglake, 1809-1891)的(Eothen, 1844)開始起算,標示著一種謙卑觀看別人,悄悄了解自己的旅行文學的進展。這個傳統,一直也藏在某些品質獨特的旅行家身上,譬如流浪於阿拉伯沙漠,寫下不朽的(Arabia Deserta, 1888)的旅行家查爾士.道諦(Charles Doughty, 1843-1926),就是一位向沙漠民族學習的人。而當代的旅行探險家,更是深受這個傳統影響,「新的旅行家像是一個來去孤單的影子,對旅行地沒有重量,也不留下影響。大部分的旅行內容發生在內在,不發生在外部。現代旅行文學比起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深刻而豐富,因為積累已厚,了解遂深,載諸文字也就漸漸脫離了獵奇采風,進入意蘊無窮之境。」這些話,我已經說過了。
現在,被觀看者的苦楚情勢已變,輪到我們要去觀看別人了。且慢,在我們出發之前,我們知道過去那些鑿空探險的人曾經想過什麼嗎?我們知道那些善於行走、善於反省的旅行家們說過什麼嗎?現在,是輪到我們閱讀、我們思考、我們書寫的時候。
在這樣的時候,是不是的工作已經成熟?是不是該有人把他讀了二十年的書整理出一條線索,就像前面的探險者為後來者畫地圖一樣?通過這個工作,一方面是知識,一方面是樂趣,讓我們都得以按圖索驥,安然穿越大漠?
這當然是填補過去中文出版空白的工作,它的前驅性格也勢必帶來爭議。好在前行的編輯者已為我做好心理建設,旅行家艾瑞克.紐比(Eric Newby, 1919- )在編(A Book of Traveller’s Tales, 1985)時,就轉引別人的話說:「別退卻,別解釋,把事做成,笑吠由他。」(Never retreat. Never explain. Get it done and let them howl.)
這千萬字的編輯工作又何其漫長,我們必須擁有在大海上漂流的決心、堅信和堅忍,才能有一天重見陸地。讓我們每天都持續工作,一如哥倫布的航海日記所記:「今天我們繼續航行,方向西南西。」
前言
這些書信,由它們的形式可以明顯看出,在當初著筆時,完全沒有要出版的意思。去年,應《休閒雜誌》(Leisure Hour)編輯的要求,在該雜誌刊出,極受歡迎,於是我決定以另一種形式將它們出版,做為極有趣味的旅遊經驗,已及急速消逝的拓荒生活的一個紀錄。
伊莎貝拉.璐西.博兒
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再版前言
為了其他女性旅者的利益,我希望對我的「夏威夷騎裝」加以解釋,那是一種「美國女子的山居裝束」──一件半長的緊身外衣,一條長及腳裸的裙子,以及土耳其式長褲,褲腳束成縐褶蓋在靴子外面-一套實用的女性裝束,完全適用於登山及在世界任何地方跋涉旅行。我在此加以解釋,並附以素描的原因,是由於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泰晤士報》(The Times)的錯誤描述。
伊莎貝拉.璐西.博兒
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三版前言
由於不小心遺漏了我在洛磯山區逗留的日期,我要借此機會加以說明。我是在一八七三年秋天到初冬時,由桑威奇群島(Sandwich Islands)回英國途中,曾在那兒逗留。信中所書,是對當地及六年前該處生活方式的忠實描述;不過,由一些六個月前曾到過科羅拉多州旅遊的朋友處得知,我第八封信中的預言很快就應驗了。小木屋已快速地被農舍取代,埃絲蒂斯公園(Estes Park)的露濕草地上也失去了麋鹿和大角野羊的蹤跡。
伊莎貝拉.璐西.博兒
一八八○年一月十六日於愛丁堡
導讀
詹宏志
「如果是那位在山中旅行的英國女子,我們可以給她一匹馬,其他人不行。」
如果你年輕時沒有勇氣享受過流浪或旅行的激情,你也許應該讀一讀伊莎貝拉.博兒(Isabella Lucy Bird, 1831-1904)的故事。
她四十歲才開始旅行,一般認為似乎是過了追求浪漫與冒險的年紀,但她卻一次又一次漂洋過海,深入異境,越走越遠,足跡來到即使是歐洲男人也罕見的地方,涵蓋的地表面積也可說是「亙古所未有」,在七十歲高齡時,她還能騎馬千哩橫越摩洛哥,一直到七十三歲她死於愛丁堡之際,她還剛剛收拾好行囊,預備再進行一趟中國的冒險旅行,只是這一次上帝臨時攔住她,她不再從心所欲,走不成了。
她從來不是一個路上的年輕人,因為她出發時已不年輕。
伊莎貝拉.博兒身處英國維多利亞時代,這個時期的女子以居家持家為尚,一般也不外出,更不強調體力活動(持扇掩口而笑或者瞪眼驚呼昏倒,都是這個時期淑女的形象),多數的女性是沒有旅行機會的。伊莎貝拉年輕時的情況也是如此,她多半時候在家以照顧病痛的父母為己任,她自己也為體弱所苦,她脊椎有病,又患有不輕的沮喪症,長年失眠;父母過世後,她年已四十,醫生建議她吹吹海風,換換環境,也就是開立了「旅行」作為藥方(這是維多利亞時代另一個令人羡慕的醫療處方)。
當時的女士旅行,指的是搭乘載客郵輪,裹著毯子、戴著遮陽帽在甲板涼椅上晒晒太陽,往地中海一帶散心的貴族文明式旅行;但伊莎貝拉野心大得多,一八七三年夏天她航往澳洲、紐西蘭,再轉赴還相當荒涼的夏威夷(即當時通稱的「三明治群島」),她的病痛在夏威夷奇蹟似地不藥而癒,不再背痛也不再沮喪;夏威夷期間,她成了第一位登上世界上最大的火山毛納洛亞(Mauna Loa,標高四千多公尺)的女性;更在這裡,她找到一種後來她主要的騎馬旅行裝扮:及踝長裙之下再加上一條土耳其長褲,以及墨西哥式馬鞍(維多利亞時代對女性裝扮也有很多戒律,有一次英國報界錯誤報導伊莎貝拉穿長褲騎馬,伊莎貝拉大為震怒,不但在書中加繪插圖顯示她的淑女合宜裝扮,更要求出版商向報社提出抗議)。
這一趟旅行不僅讓博兒女士從此三十年醉心旅行,也從此造就了一位世人愛戴的旅行作家。她在三明治群島旅行的過程中,持續寫信把旅行見聞與心境描繪給她的妹妹涵蕊雅塔(Henrietta,或Hennie),這些信札後來改編結集為《在三明治群島的六個月》(Six Months in the Sandwich Islands, 1875),書在當時受到的注意並不大,但它透露了作者獨特的才氣,一種熱情洋溢充滿感染力的寫作風格,也開啟了一個廣受歡迎旅行寫作者的道路。
伊莎貝拉在三明治群島的旅行之後,嘗到旅行的滋味;她曾經在論及旅行時說:「它(旅行)像活在一個新世界,如此自由,如此新鮮,如此生氣勃勃,如此無憂無慮,如此無拘無束,……你連睡意都不情願。」她是真正愛上旅行的人,此後的三十幾年,她幾乎沒有太多時間是放下行李,她回家好像只是為了把旅行記錄下來,連絡一下出版社,除此之外她總是在路上,先是在美國洛磯山脈,然後是當時還鮮少外人旅行的日本,接著是馬來西亞,波斯,埃及,中國,西藏,最後是環遊世界。中間她曾經停下來完成婚事(嫁給比她小十歲的一位醫生),家庭生活把她拘束在家裡幾年,她曾經計畫探訪新幾內亞,但旋即作罷,她開玩笑說:「這不像是個適合帶丈夫去的地方。」
她後來的旅行成就是巨大的,她走的道路不僅是不曾見過歐洲女性,有時連男性也不曾出現。譬如她在一八七八年遊日本,取道日光,走裡日本東北區,進北海道,歷時四個月,騎馬一千四百哩,寫成她的名作《日本僻徑》(Unbeaten Tracks in Japan, 1880),這都是西方人前所未見的行動。這些成就,使她成了第一位受英國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邀請演講的女性,也是該學會第一位女性院士;而在英國女性還沒有投票權之前,她已經應英國國會之邀,在國會殿堂上向國會議員演講她的波斯之旅。
但伊莎貝拉.博兒對旅行史更大的影響,我懷疑不是旅行本身,而是她對旅行的追求熱忱以及對女性同胞的鼓舞。
相對於維多利亞時代對女性角色的局限與禁錮,伊莎貝拉的確是在異鄉旅行中找到個體的自由與個性的發揮,她自己就曾經說:「旅行者有特權去做最不合宜的事。」伊莎貝拉也描述自己的旅行,是以一種「無所不宜,行動自由的風格」(an up-to-anything and free-legged air),這樣的處境毋寧是對她身處時代的一種反動,一種隱性的對抗,一種不明顯的爭自由,爭女權。
伊莎貝拉.博兒的這個風格,在她的《山旅書札》(A Lady's Life in the Rocky Mountains, 1879)一書大概是表露得最為明白,這本記錄她在一八七三年美國洛磯山脈漫遊的書信集,不但使她成為十九世紀舉世愛戴的旅行作家,也被史家看作是最足以代表伊莎貝拉的經典之作。
在夏威夷群島初嘗旅行滋味時,伊莎貝拉已有遊洛磯山的計畫,一九八三年自舊金山登岸而成行,她一如往例,行程中隨時以長信向妹妹描述旅行所見所感,這些信札先是在雜誌上發表,後來才結集成冊。這部書記錄美國西部仍然狂野不羈的大自然景致,粗獷的人情與村俗,以及自己一個英國女子的旅行遭遇,更有意思的,這當中還包含一場與亡命之徒的浪漫戀曲(這是後來伊莎貝拉的其他書中所沒有的)。
當時的洛磯山脈還是一塊未被馴服的野地,鐵路才剛建好,處女地上住的是各種幹粗活、喝烈酒的硬漢和拓荒者,那裡有一種尚未為文明所軟化的純樸強悍民風,而大自然更是炫爛多彩,粗礪、危險但美麗,伊莎貝拉的堅毅和優雅,闖入了這麼一個環境,讓整個環境與住民(多半是男性)都起了微妙的變化;而在伊莎貝拉的細膩捕捉之下,這些情境與情景都被呈現了出來。伊莎貝拉在這些書札中,不管寫夕陽,寫山色,寫雪落,寫草長,都讓人讀得心醉;這其中,又穿插了她結識的「親愛的亡命之徒」(Dear Desperado)吉姆,獨眼,暴烈,英俊,歌聲甜美,卻又時時酗酒。伊莎貝拉毫不保留地寫出自己心中的激情與掙扎,一方面她覺得他「如此可愛又如此恐怖」,一方面則自我分析說:「他是那種所有的女人都會愛上,但沒有一個理智女性會下嫁的男人。」畢竟,伊莎貝拉是維多利亞時代教養出來的理智女性,她終究沒有答應他下嫁,她與這位亡命之徒並肩騎馬於草原之中,共同觀賞斷崖絕景,一起克服野外生存的困難,但她,仍舊困難而黯然地拒絕了他。
洛磯山壯麗景色加上柔腸寸斷的戀情,何等浪漫的邂逅遭遇;但也不能掩蓋這位奇女子融入粗獷環境的毅力與堅忍,所有的村民也都最後尊敬並認同這位「英國女子」,當伊莎貝拉一次託人向驛站借馬,站中駐防者就說:「如果是那位在山中旅行的英國女子,我們可以給她一匹馬,其他人不行。」
這本書的出現,感動了所有的讀者,也激勵了所有的女性,在伊莎貝拉.博兒之後受啟蒙、鼓舞的女性旅行者不知凡幾;在眾多女性旅行者當中,不斷被閱讀、被討論,或者研究她的意義,追躡她的足蹤,她的傳記恐怕也是女性旅行者最多的,她是一位永遠引人興趣的人。如果你有機會前往日本旅行,在日光著名的金谷旅館走廊裡,仍然掛著她的畫像,這是一百多年前她下榻的地方,你會覺得典型不遠,一個奇女子仍然活在眾人的心中。
 中醫臨床經典叢書:金匱要略
中醫臨床經典叢書:金匱要略 中醫體質養生隨身查
中醫體質養生隨身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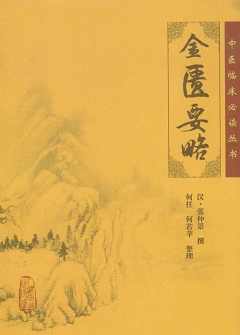 金匱要略
金匱要略 古醫籍稀見版本影印存真文庫:金匱要略
古醫籍稀見版本影印存真文庫:金匱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