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武軍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動 | 生病了怎麼辦 - 2024年11月

神武軍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動
本書為“哈佛——燕京”系列叢書之一。哈佛燕京學院建立於1928年,總部設在哈佛大學。和大多數帝國一樣,明王朝也喜愛炫耀武力,以彰顯國家的強盛和力量。明朝的前兩百年裡,皇室的尚武展示活動在當時的詩歌、散文、繪畫中均有呈現,同時也反映了當時皇帝與權臣關於治國術、軍事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等諸多問題的不同觀點。本書對於中國明代皇家以狩獵為中心的軍事傳統、尚武風氣、軍事文化都有描繪,視角迥異于中國明史學者,頗有可讀性,也很有啟發意義。
魯大維(David M. Robinson)
美國柯蓋德大學何鴻毅家族基金講座亞洲研究暨歷史教授、富布萊特學術交流基金會訪問學者。研究方向包括蒙古帝國史、軍制史以及近代東亞的外交實踐等。著有《帝國的暮光:蒙古帝國治下的東北亞》《匪徒、宦官與天子:明中期的政治叛亂與經濟暴動》《亂中求治:韓國理學家鄭道傳及其時代》等。
致謝/圖片清單/明朝皇帝清單
導言
第一章 明初的皇室田獵
第二章 皇室田獵的諸般形象
第三章 騎術與箭術
第四章 對尚武活動的新看法:明朝的第二個百年
第五章 明代皇室的獸苑和獵苑
第六章 結論與延伸
參考文獻/索引
在中國歷史上,明王朝(1368~1644年)在諸多場合通過各類媒介頻繁展示它的權力和正統性。氣勢恢宏的皇宮建築群和巍峨高聳的京師城牆十分顯眼,它們都真實地展現了王朝的權勢和巨大財力。一整套儀典系統則凸顯了皇帝淩駕于萬人之上的獨特地位及其在整個國家中的核心作用。他對經典學問的獎賞和對“正統”思想信念的支持,則反映了他作為正統觀念和道德規範的維護者的權威。朝廷中負責起草詔命、編纂史冊和輯錄政令的“詞臣”,也會賦詩作文來歌頌朝廷的威嚴、君王的功德以及皇天的庇佑;這些作品將在朝堂、京師乃至整個國家被廣泛傳閱。朝廷官員時常提醒臣民:皇帝及其臣僕愛民如子,為了百姓的福祉,他們不知疲憊地辛勞著。最後,朝廷頒佈了數以萬計的詔令,涉及諸多議題,如規定臣民的服制、劃定可崇奉的神明的範疇、懲治貪官污吏、獎賞貞女節婦、賑濟災荒、斥責不歸化的夷酋,等等。這些詔令宣示了朝廷的權威:朝廷明白何為正確,並能使一切事務各安其位元。簡言之,同幾乎所有其他王朝一樣,明朝也致力於推動一場本質上永無止境的教化運動。
本書所要考察的就是這種教化運動的一個方面——明朝中前期一系列被我稱為“尚武展示”(martial spectacles)的活動。更確切地說,尚武展示活動指包括皇室田獵、騎術表演、馬球比賽、射藝比武、閱兵典禮以及皇室獸苑等在內的一系列活動及設施。之所以聚焦於它們,是因為它們有助於我們準確地把握近代早期的宮廷文化、亞歐大陸的展示傳統以及明廷內部對皇位和權力的爭奪情況。為了做到全景展現,不能把本書考察的這些尚武展示活動簡單歸於任何一項當代明史研究的類目。近年來的漢語學術成果通常認為,像射箭和田獵這樣的事項只是宮廷活動或娛樂消遣。而明清時期的作品則將皇室田獵和軍事檢閱(通常包括射藝比武)列為軍禮。馬球比賽由皇帝主持,通常在端午這樣的歲時節令裡舉辦。而獸苑和獵苑等都屬於實體設施,需要日常維護。
那麼如何才能證明,將這些不同的活動和場所統稱為“尚武展示”是合理的呢?這些尚武展示活動具有諸多共同特徵。幾乎所有的這些活動都離不開精研的技藝、牲畜的使用、人多馬眾的表演者,以及作為觀眾的京師達官顯貴。無論是馭馬騎射的高超技藝,還是進行獵殺時的兩相協同,大多以展現威猛勇武為重點。不管是就活動本身還是就面向大量觀眾的展示而言,皇室獸苑和獵苑在某種程度上都與上述活動有所不同。但是,文獻中記載的那些論辯的片段賦予了它們諸多意義,而且它們與通常得自異邦統治者的貢物和軍事演練密切相關。詩詞歌賦和畫像讓這些場景被傳播給廣泛的觀眾群體,使它們不再被局限在那些親臨現場者之間。就像本書所考察的其他尚武展示活動一樣,對獸苑和獵苑的研究也基於君王對人(將珍禽猛獸進呈于君主的人)和獸的掌控。
我們最好將尚武展示活動理解為君主關於展示與軍事傳統的豐富“庫存”中的一部分。登基、喪葬、立儲、大婚、新年祭祀、皇帝耕藉和皇后親蠶以及行孝禮等活動一般在紫禁城中或郊外舉行,華麗的車輿、身著盛裝的皇親國戚以及他們的侍從各就其位。尚武展示活動根植於軍事表演和軍禮的傳統,包括軍舞軍樂、向君王獻俘、拜將、祭旗、祈求凱旋的祭禮以及在戰事前後告祭太廟。無論是在宮中還是在巡行途中,明朝皇帝都時刻受到保衛。禁軍不僅保障安全,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營造出一種莊嚴之感。在京師之外,明廷的艦隊七下西洋,到達了東南亞、印度洋,最遠航行至非洲東海岸,當然這也是面向廣大國際觀眾的耗資靡費的武力展示。
尚武活動耗資不菲。事實上,它們顯示了皇帝在舉辦奢靡活動一事上的優於潛在對手的實力。在明代不同的時間節點,這些潛在的或實際存在的對手包括:異邦敵患、野心勃勃的國內將領、心懷二志的地方勢力(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老謀深算的朝中大臣、胸懷怨憤的皇室宗親。有關大閱禮,也就是皇宮中舉行的常規大規模軍事訓練和檢閱的詳細財政資料已不可考(大量清代檔案顯示,這類材料已丟失數百年)。但據官方編纂的王朝編年史《明實錄》記載,在16世紀中葉舉行的兩次檢閱之前,軍士們曾分別被賞賜一萬兩和三萬兩白銀。明代的文人宣稱,1569年的檢閱耗資“兩百萬兩”白銀,而在17世紀早期的一次檢閱中,修造一架可用于攀爬京師城牆的器械就花費了“數萬金”。另外,皇帝還會賞賜絲帛和銀質軍功章,並宴請自己喜愛的人。校場上的將士穿著統一的服裝,揮舞著朝廷配發的兵器,騎著各營供給的馬匹。檢閱(以及田獵、射藝比武、馬球表演)中的這些士兵本身也成了可供君王調配的一種政治和軍事資源。16世紀中葉的檢閱一般都有數萬人參加,更有記載稱1569年的檢閱有十二萬人。通常有上百人參加圍場田獵,有時還會有上千人參與。這些尚武活動顯示出皇帝讓人依指令和能力行動的權力。
在亞歐大陸的其他地方,我們也能發現類似的情況。基於17世紀、18世紀莫臥兒王廷和清廷行帳的情況,喬斯·戈曼斯(Jos Gommans)總結道:“由於行帳能夠長久地在帝國全境內宣揚王權的威嚴,因而實際的戰爭通常能夠避免。凡王廷所到之處,百姓都趨於順從。”雖然統治者為展示其在財富和人力方面的資源優勢耗費巨大,但這也比一場大型的軍事衝突或者宮廷政變的代價要小得多。皇室田獵、馬球比賽、射藝比武這些活動,不僅具有娛樂消遣的功能,同時也發揮著提醒統治者的作用:軍事力量仍是王朝的中心支柱。
要理解這些尚武展示活動,就應該將其置於明朝與北元及草原上的其他蒙古政權之間深度互動的背景之下。北元是學術界中一個便捷的慣稱,用來指代在統治中國近一個世紀後,於1368年從北京敗退回草原的成吉思汗後裔的政權。北元人自稱是忽必烈(更籠統地說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後裔,因而在14世紀晚期仍保有巨大的聲望,掌控(有時僅僅是間接掌控)著強大的軍隊。在亞歐大陸的東端,明與北元陷入了一場爭奪正統性和認同感的政治博弈,而展示朝廷的壯觀威嚴正是這種博弈的一部分。
從更為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說,馭馬之術和騎射技藝在明元之間的軍事對抗中是至關重要的部分。在中世紀和近代早期,弓騎兵一直是內亞及周邊地帶最為重要的軍事力量。相較而言,草原遊牧政權更容易獲得大量優質駿馬和從小接受騎射訓練的男丁。而西亞、南亞和東亞的農耕政權所飼養的馬匹通常在數量和品質上都較為遜色,所以他們只好利用經濟資源上的優勢來換取草原駿馬作為補充。因此,儘管身處21世紀的觀眾們可能認為高科技武器才是衡量現代閱兵的黃金標準,馬匹更多是供表演之用的,但在當時,草原周邊的政權在殘酷的戰爭現實中體會到了馬匹在軍事上的重要性。隨著相關技術的改善,火器的軍事地位不斷提升,然而在近代早期,弓騎兵對內亞大多數政權來說仍不可或缺。
展示活動
作為歷史上大多數政權的共有元素以及當今政治舞臺的突出特點之一,展示活動已從多方面被詮釋過了。關注14~18世紀的西歐的學者創作了許多關於展示活動、統治者和權力等內容的優秀作品。羅伊·斯特朗(Roy Strong)在其經典著作《宮廷的輝煌:文藝復興時期的盛會與權力舞臺》(Splendor at Court:Renaissance Spectacle and the Theater of Power)中,描述了宮廷節日中的入場式、假面舞會、煙火表演、雕塑、繪畫以及芭蕾舞劇等。斯特朗提出:
借此,國王能夠在臣僕眼前展示他最高貴的一面。通過附會神話寓言、營造符號象徵和展現儀態舉止,節慶成了一種頌揚君主榮耀的方式。如此一來,神聖的君主制的真理能夠被散佈於宮廷,而順從的貴族也能夠在儀式過程中安分守己。
將巡行、集會以及演出理解為一種表達王權的方式的人,遠不止斯特朗一個。依據16世紀義大利的情況,邦納·米切爾(Bonner Mitchell)同樣發現,市民盛會的主要功能就是“向市民及外邦人展示國家的最高權威”。另外,羅伯特·埃文斯(R.J.W.Evans)也提到,“集會也許是展示統治者權勢以及有序統治的重要武器”。
但也有學者對這種將集會和演出視為單純的權力展示的觀點無法贊同。他們重新檢驗了關於“順從的貴族”的假設,強調市民盛會中的那些具有多重含義且富有對抗性的元素。正如傑倫·杜因達姆觀察到的,“雖然君主有意識地使用虛禮提升權威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將儀典當作完全由君主控制的、不受等級觀約束的活動,沒有任何助益”。約翰·亞當森(John Adamson)的論調則略有不同,他告誡我們,不要把宮廷文化降格為“政治宣傳”,它並不是要向8溫順的觀眾反復灌輸連貫一致的政治價值。其他的學者,如邦納·米切爾和馬康·韋爾(Malcom Vale)則認為,儘管巡行等活動凸顯了君主的權勢,但它們通常也包含了對地方精英之特權和地位的承認。另外,杜因達姆、韋爾和亞當森反對貴族被君主玩弄于股掌之中的謬論;西德尼·安格羅(Sydney Anglo)則強調認知和傳播的問題,他告誡說,並非所有觀眾都能理解這些視覺上和文本上的複雜隱喻。最後,凱文·夏普(Kevin Sharpe)著有一本涉獵廣泛又極具洞見的書,書中討論了都鐸-斯圖亞特時期的英格蘭的權威與形象。他在書中指出,有必要去“認真思考他們試圖用文字和繪畫營造出的都鐸形象,來掩蓋的那種焦躁不安”。
總的來看,這些專注於中世紀晚期及近代早期的西歐宮廷的研究反映,在對展示活動進行考察時必須時刻謹記以下內容,以免犯過度假設的錯誤:這些展示活動以及其他經營王朝之努力的效果、意圖和動機很少不言自明;它們常遭篡改和曲解;最後,它們在傳達出宮廷權威和榮耀的同時,也同等限度地揭露了統治者的恐懼和脆弱。不是所有人都對宮廷的宣傳買帳。這些作品儘管在研究展示活動的創造、傳播及受到的質疑等方面相當縝密,但經常忽視王公大臣的作用——他們常常被刻畫得像文書人員一般。近來的研究常常聚焦於“國家”及其擴展和控制權力的整體努力。明朝尚武展示這個案例則揭露了朝堂內的諸多爭議,因為皇帝的利益和立場與高官大臣常常相左。
尚武展示活動還需要觀眾們的響應。出席馬球比賽、射藝比武以及軍事檢閱的朝臣們並不只是在觀賞。基於20世紀美國政治和社會的個例,邁克爾·哈洛倫(Michael Halloran)強調這種展示是一種“生活體驗”,他指出“參與這種展示活動的經歷早已是維持社會秩序的一種規制”。哈洛倫強調了觀眾觀賞展示活動時的反應所具有的重要影響。通過參與這些活動,觀眾構成了一種共同體。明朝的高品秩文官在皇室展示活動等場合中歌頌君王,為這些盛事賦詩作文,事實上是在通過親身參與,表明他們接受了一種特定形式的皇權及他們與皇帝的那種特殊關係。因此,對朝廷高官來說,這些尚武展示活動促成了他們對權力結構的明確承認(以及事實上的永久維持)。
以上內容使我得出了本書的第一個核心論點:統治權必須要展現出來,而不是一種抽象的存在。明朝皇帝通過政治決策、軍事征戰、聖旨詔書以及尚武展示(僅舉幾例)等方式來宣示皇權。他們不會也從未設想過,他們的地位無可爭議或者他們的旨意可以暢行無阻。正如諾伯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就帝王威望進行研究時所發現的,統治者的權勢必須通過定期的宣示及承認來維繫,但宣示權力之時也恰恰是權力十分脆弱之時。這些尚武展示活動如果被譏笑、敷衍、抵制,就會使統治者威信掃地。西元前1世紀時,狄奧多羅斯(Diodorus)就曾通過嘲笑敘利亞的安條克四世(Antiochus Ⅳ of Syria,前215~前164年)失敗的展示活動,來貶低安條克四世作為統治者的政治合法性和地位。“安條克的有些想法和行為是高貴而驚豔的,”他寫道,“有些卻是如此低俗而愚蠢,以至於所有人都十分鄙夷他。在慶典活動的比賽中,他竟採納了與其他國王相反的規則。”所以,這些盛典不僅是盛大的娛樂活動和宣示王權的場合,也是王權面臨挑戰的地方。
作為一種統治手段,這些尚武展示活動展現了皇帝對人與獸的掌控能力。人與獸被安排去參與盛大的田獵和檢閱活動,依照皇帝的命令列動,從而實現皇帝的意志。軍士們選拔自皇帝的軍隊,牲畜則由皇室馬廄、獸苑提供,或者由外藩(作為貢品)進獻。尚武展示活動顯示出統治者對軍士及其才能的洞察力;他評定軍士的馭馬和射箭水準,嘉獎他們在狩獵中的勇氣和實力。在這些尚武展示活動中,皇帝還通過為臣屬提供奢靡的娛樂活動以及為參與者提供豐厚的獎賞,來彰顯他的慷慨大方。
在大部分地方和時代,控制力、洞察力以及慷慨大度都是作為統治者的必備素質。在豐富多樣的中國傳統中,帝王也總被期望擁有這些品質,但我們一直以來可能更關注它們在“文”的層面的表達方式,尤其是在研究帝制晚期時。如果明朝的君主能識忠良且知道通過寵信、給予官職及恩賞來栽培俊彥之士,他們就被認為是英明的。尚武展示活動清楚地表明,這些品質在“武”的層面同樣重要,儘管文人們可能悄悄略過了這一事實。這種文與武的不協調關乎本書的第二個核心論點。從總體上講,尚武展示活動幫助定義了皇帝、臣僕以及作為整體的朝廷的身份特性。尚武展示作為娛樂活動,吸引了大量觀眾,但也塑造了觀眾的認知,影響了他們的行為。斯科特·休斯·邁爾利(Scott Hughes Myerly)注意到,19世紀英軍奢華的典禮招來大量觀眾,他們為軍樂團、華美制服以及人騎協同行進所吸引。他認為這些尚武展示活動有助於提升軍隊形象在劇院、音樂、玩具以及社會組織中的流行度。在明王朝的例子中,田獵活動、軍事檢閱和獸苑不僅反映了人們對皇權的態度,也有助於我們理清皇帝的活動與他憂心的問題。一位在馬上搭弓射箭,或于獵場逐鹿,或飼養珍禽猛獸的帝王,他能讓人信服嗎?後面的章節將表明,明代中國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因時而異,且這些不同的回答直接塑造了“天子”的意涵。
同樣,高官文人們回應宮廷尚武展示活動的方式,也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身份。他們會為皇帝迎接來自海外的白象而賦詩祝頌嗎?他們會稱頌、批評或者嘲諷于紫禁城內精心籌備的檢閱嗎?他們選擇性地發揮自身文學才能的方式,定義了他們與君王的關係、他們作為朝中大臣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們對自己身系王朝興衰的儒士身份的理解。正如竇德士對江西官員的研究以及最近哈利·米勒(Harry Miller)有關國家與士紳間衝突的著作所顯示的,這些身份認同問題既非一成不變,也非對所有官員都普遍適用。對尚武展示活動的回應提供了一條探尋相關變遷與差異的路徑。最後,皇室田獵、馬球比賽和禮物交換,都是明廷在廣闊的東亞大陸舞臺上協調其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方式。因此,尚武展示活動不僅反映身份,還幫助塑造身份。正如文化人類學家柯利弗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觀察到的,“統治的表裡之間原本明晰可辨的界限變得越來越不明顯,甚至越來越不真實;真正起作用的是它們相互轉化的方式,它有點像品質與能量間的轉化”。
後面的章節將詳細討論,雖然明代宮廷存在田獵、馬球比賽、馭馬以及其他展示活動的特定先例,但宮廷文化是個人能動性與長期歷史模式的共同產物。35尚武展示活動在特定時期的具體表現形式是以皇帝個人及其近臣的喜好和想法為依據的。與此同時,所有的明朝皇帝都充分發掘並利用了明以前的歷朝歷代在宮廷傳統和實踐方面的歷史積澱。也許個別因素的近源可以追溯到契丹、女真和蒙古統治者所建立的王朝,它們在10~13世紀崛起於蒙古草原和現中國東北的森林;或者也可追溯到像宋(960~1279年)這樣的中原王朝。對15世紀、16世紀的明朝皇帝來說,由列祖列宗所確立的先例,也就是宗室傳統,是一塊關鍵的基石。一方面,契丹、女真、宋、蒙古以及明朝初期的宮廷相互影響;另一方面,它們都吸收、借鑒了可追溯至更久以前的皇權觀念、朝廷禮制以及權力和威嚴的象徵。
不管是就一般層面上的明代宮廷文化而言,還是就特殊層面上的尚武展示活動來說,我的目標都不是追根溯源。我們完全可以承認,類似“中原”或“草原”這樣的概念,也許在特定時間和情境裡,在修辭意義和意識形態層面有巨大影響力,然而,研究者應當保持謹慎,避免誇大其作為分析性類別的效用。到洪武帝(1328~1398年)稱帝的1368年為止,中原王朝和草原政權已經交互影響了兩千多年。這些互動包括了一系列的積極模仿、借用、明顯拒斥和悄無聲息的重新定義。因此與大多數前朝皇帝一樣,明代統治者採用了一套複雜的做法、觀念和象徵符號,人們並不完全瞭解它們的最初形態以及隨時間推進而發生的轉型,即便是那些勤勉的會典編纂者也沒辦法確認,儘管他們表面上將政治和儀式制度追溯到了有歷史記載之前。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重要的論點是,我們需要用一個廣角鏡來審視明代宮廷乃至整個明王朝。站在共時性的角度,只有與亞歐大陸東部的其他地區,尤其是內亞腹地的發展相對照,明朝歷史的諸多元素才能變得明晰。界定明朝第一個百年的,是其與元政權及元在草原上的繼承者的相互較量。接下來的章節將證明,尚武展示活動常常是為皇宮和朝堂之外的觀眾準備的,這不只是洪武帝和永樂帝(1360~1424年,1402~1424年在位)治下的情況,在明朝的前兩百年歷史中都是如此。
站在歷時性的角度,我們最好將明廷置於長時段的歷史中去理解,而且早就該重新評估它與其前朝元和後朝清的關係了。一段描述西歐在中世紀晚期的情形的文字,指出了許多甚至大部分宮廷所共有的一些特徵。馬康·韋爾寫的是英格蘭王國、法蘭西王國和低地國家的宮廷:(它們)通常接受“外國的”影響——這樣做的代價越發昂貴——也對異質的和外來的影響保持開放。因此,它們往往容易在某些臣民中引起怨恨和排外的情緒,激起針對宮廷的異化和奢靡之風的“民族主義”情緒。宮廷是一種媒介,一定程度的國際主義和世界主義經由它被傳播至社會——包括教會與世俗社會——的上流階層……統治中心位於今天的中國的諸多王朝,也許也可以簡單地用類似的措辭來形容。比如說,唐朝的世界主義一直得到公認。最近,許多學者都在強調清朝的多民族特點,並且將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皇帝對漢、滿、藏以及西歐的學問、語言、宗教、技術和藝術的積極支援態度上。最後,吐蕃、突厥、鮮卑、女真和蒙古這些所謂的“征服王朝”,它們的興起都展現了很強的文化雜糅、吸收和借用的特性,它們能通過對風格迥異的行為、觀念和技藝進行重塑,來回應不斷變化的政治、軍事和精神需求。
那麼,明朝在哪些方面也符合這種文化雜糅的特點呢?當我們認為明廷內向且排外,或者說對域外的土地和人口漠不關心之時,其實我們在做一種對比,即我們在比較明代宮廷和元清兩代的宮廷。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最近幾十年來,清朝逐漸被認為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多民族帝國,其皇帝有意識地將自己置於一系列宗教、政治以及意識形態傳統的中心位置。而元朝同樣憑藉其在亞歐大陸貿易體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享有盛譽,在其統治下,人員往來、財貨流通,以及宗教活動、統治理念和知識結構的交流互動,都達到了空前的水準。
當我們像這樣進行綜合考慮後,無論是籠統地討論明王朝,還是特指明代宮廷,明給諸多研究者留下的印象都是孤立且內向的。杉山正明(Sugiyama Masaaki)這位研究蒙古帝國的日本頂尖學者,將明朝的老氣橫秋、萎靡不振、畏葸不前與元朝的活力四射、幅員遼闊、胸懷四海做了對比。宮紀子(Miya Noriko)同樣指出,早期的明朝目光短淺,一個突出的變化反映在它對“天下”的地理認知遠不如前朝。著名學者羅茂銳(Morris Rossabi)也認為,及至15世紀中葉,明王朝對中亞已經興味索然。
杉山正明、宮紀子、羅茂銳等學者無疑是對的,比起元清兩朝,明朝確實缺乏世界性,與外國的深入交流不足,在亞歐大陸的舞臺上顯得不夠自信。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它始終都是孤立封閉、內向排外的。如果我們回到韋爾的評估尺度上,就會發現明廷其實比我們通常認為的要更具世界性,它更深入地參與了亞歐大陸的事務。從14世紀到16世紀早期,皇帝們常常因為持續而慷慨地支持藏傳佛教這樣的外來宗教、在京師修建寺廟、資助成百上千的藏僧而備受詬病。同樣,在明朝統治的前一百五十年裡,它對北元及其繼承者來說都是強大的競爭對手:明朝竭力使亞歐大陸的其他地方相信天命已易;明廷不論出身,唯才是舉;它承諾會尊重亞歐大陸的其他政權在元朝治下曾享有的地位和特權;它也試圖表明自己在整個區域內都有足夠強大的軍事實力來抗衡蒙古勢力。延攬並任命蒙古人為明軍高級將領便是實現上述目標的一種手段。
明廷世界性的一面有時被接受,有時則受到指責。朝廷對蒙古人及其後裔的任用,就反復遭到明朝文人們的批評。直到16世紀中期,明廷都一直維護著一座獸苑,那裡有從遙遠的撒馬爾罕和安納托利亞送來的大型猛獸,此事也一再激起一些朝臣明顯的憤慨。韋爾早已言明,世界主義及親近異域事物的行為也許容易招致某些臣民的反對。在不同的時期,皇帝對西藏、蒙古和中亞的信仰、人物、飛禽走獸的興趣(還有這種興趣表像下的與中亞統治者的聯繫),都遭到了朝中文官們的批評。
本書還會探究元明清三代宮廷文化之中具有驚人延續性的部分。如果我們拒絕將少等同於無,如果我們不誇大內亞(或北方的征服者)與中原政權之間的差別,如果我們注意到明代宮廷文化中被忽略的部分,就能領悟騎術和皇室田獵在元明清三朝的重要性,以及作為軍事統帥的皇帝在深層次的行為和信念上所具有的那種顯著延續性。
雖然關於其他地區宮廷文化的比較研究和整體研究近期成倍增加,但對明代宮廷的系統性研究仍然缺乏。在於總體框架下對近代早期的宮廷做出中肯評價成為可能之前,對明代宮廷的權力和統治做一次細緻瞭解是必不可少的。它們是何以產生、協調、延續的?它們何以被展示、傳播、爭奪?皇室宗親、朝廷重臣、官僚體系、地方精英及京外的臣民是如何看待並嘗試利用皇權的?皇權如何與宮廷文化相關聯?這些都是具有深遠意義的問題,有助於增進我們對明代宮廷和更廣泛的近代早期宮廷的理解。
近些年來,學者們已開始深思明朝京師宮廷文化的輪廓,探究它與各藩王王府之間的關係,以及與更廣義的明朝歷史發展的聯繫。明朝宮廷不僅包括位於北京(15世紀初之後)的皇宮,還包括留都南京的宮廷以及各藩王王府。冒著過度暗示行政層面的一致性的風險,我暫時把這三類地方和它們的行為禮儀都放到一個總的明朝宮廷系統下。雖然這三類宮廷在規模、立場、功能上差異很大,但是最新的學術研究表明,從儀式運用、行政規程、人事任免及共同利益的角度出發,這種把它們放在一起看待的視角是合理的。最後,儘管我討論了明朝開國皇帝的宮廷,也將各藩王王府納入分析,但是本書的關注點還是集中在北京的宮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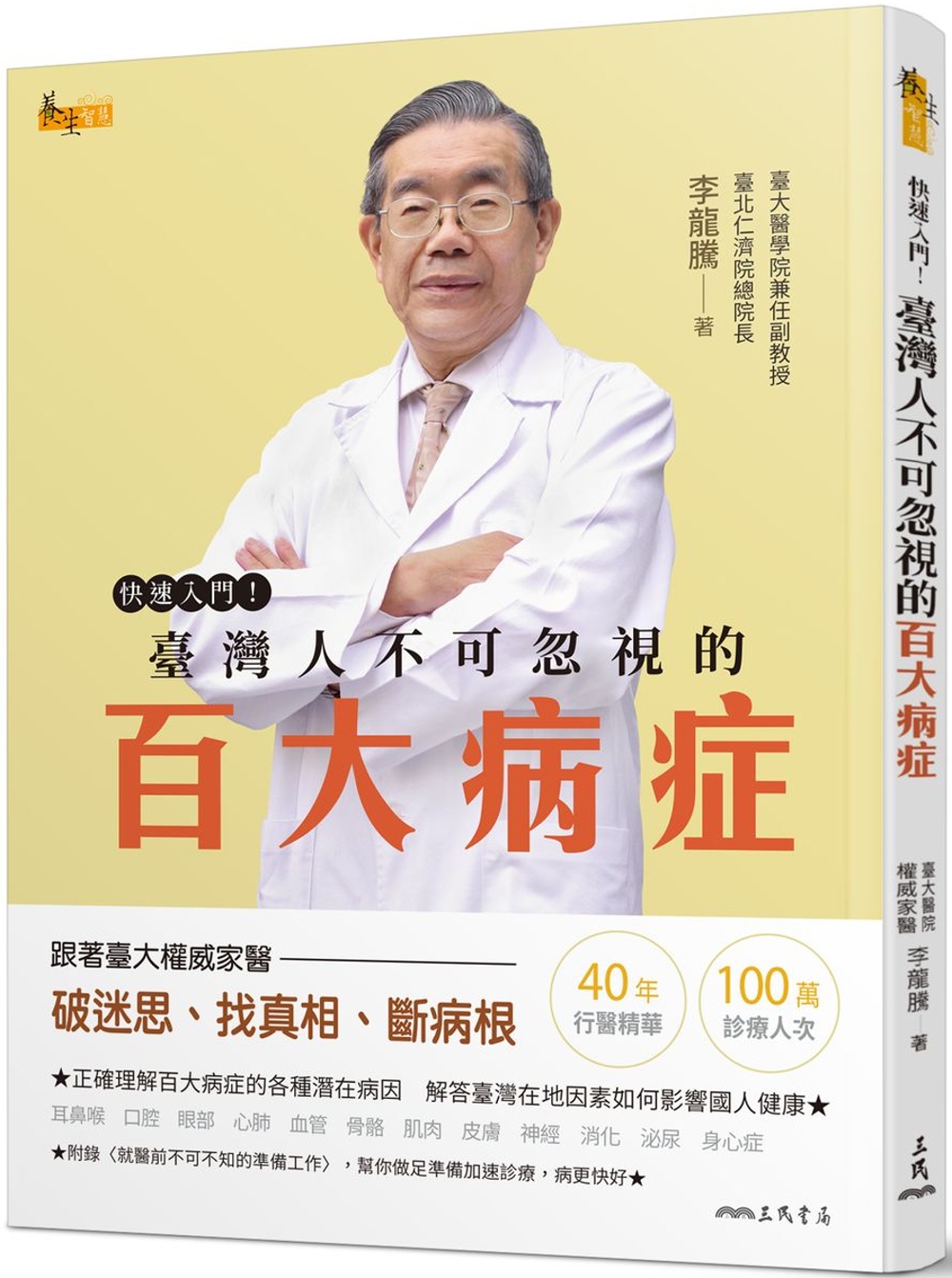 快速入門!臺灣人不可忽視的百大病症
快速入門!臺灣人不可忽視的百大病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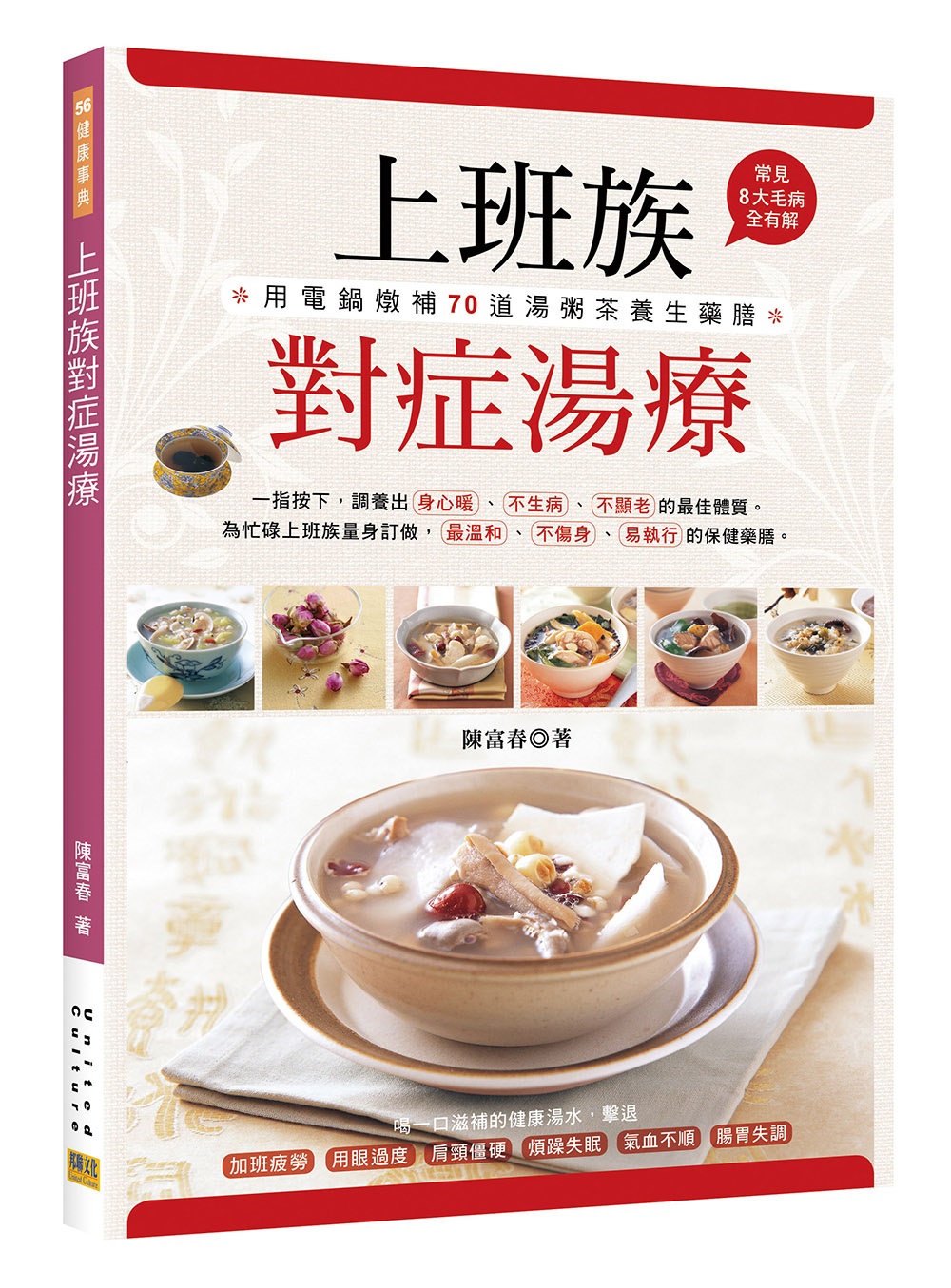 上班族對症湯療:用電鍋燉補70道湯...
上班族對症湯療:用電鍋燉補70道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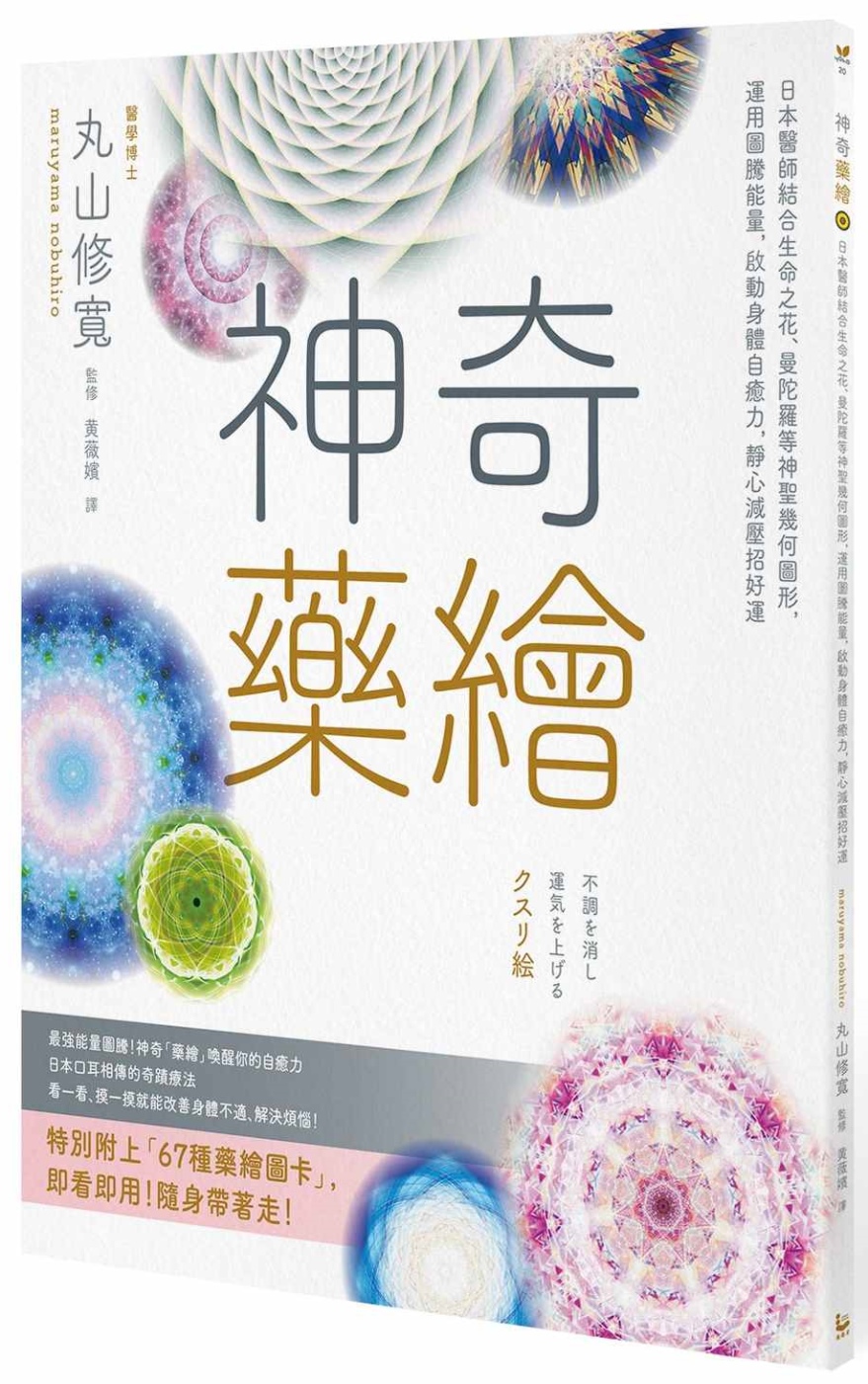 神奇藥繪:日本醫師結合生命之花、曼...
神奇藥繪:日本醫師結合生命之花、曼... 莊雅惠 好好調養你的五臟:用新思維...
莊雅惠 好好調養你的五臟:用新思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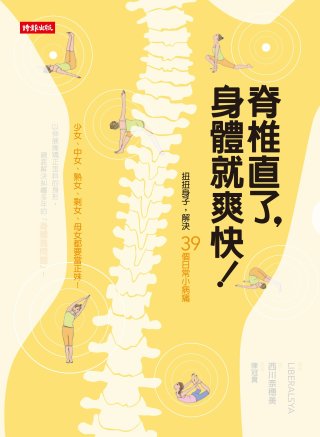 脊椎直了,身體就爽快!:扭扭身子,...
脊椎直了,身體就爽快!:扭扭身子,... 抗藍光眼鏡 BOOK(晶漾白)-低...
抗藍光眼鏡 BOOK(晶漾白)-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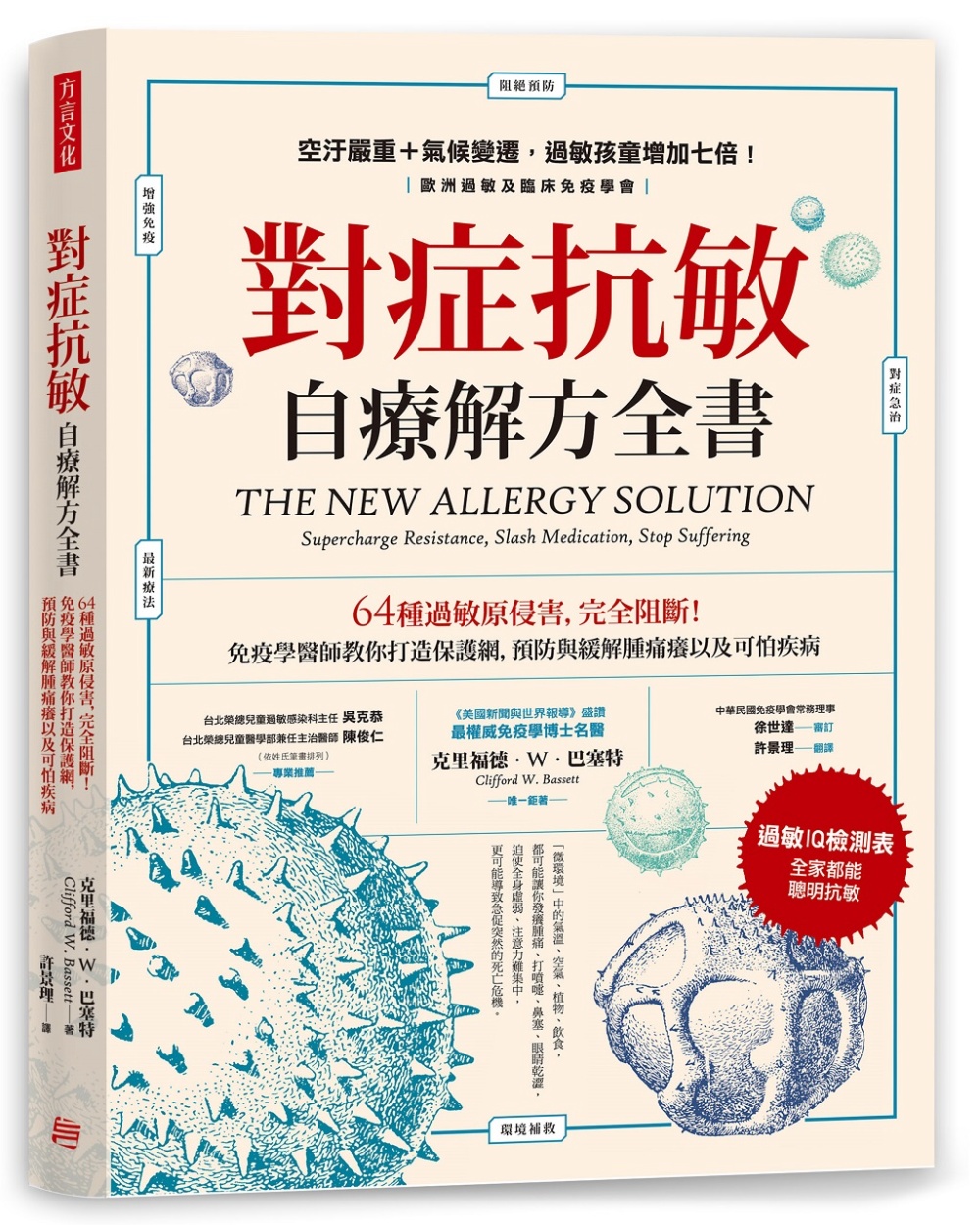 對症抗敏 自療解方全書:64種過敏...
對症抗敏 自療解方全書:64種過敏... 外罩式抗藍光眼鏡 (豹紋限定款):...
外罩式抗藍光眼鏡 (豹紋限定款):... 全彩圖解消除眼睛疲勞、拯救惡視力!...
全彩圖解消除眼睛疲勞、拯救惡視力!... 玻璃罐排毒水【法國藍帶甜點師獨家配...
玻璃罐排毒水【法國藍帶甜點師獨家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