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大流行:歷史、統計數字,用藥與患者 | 生病了怎麼辦 - 2024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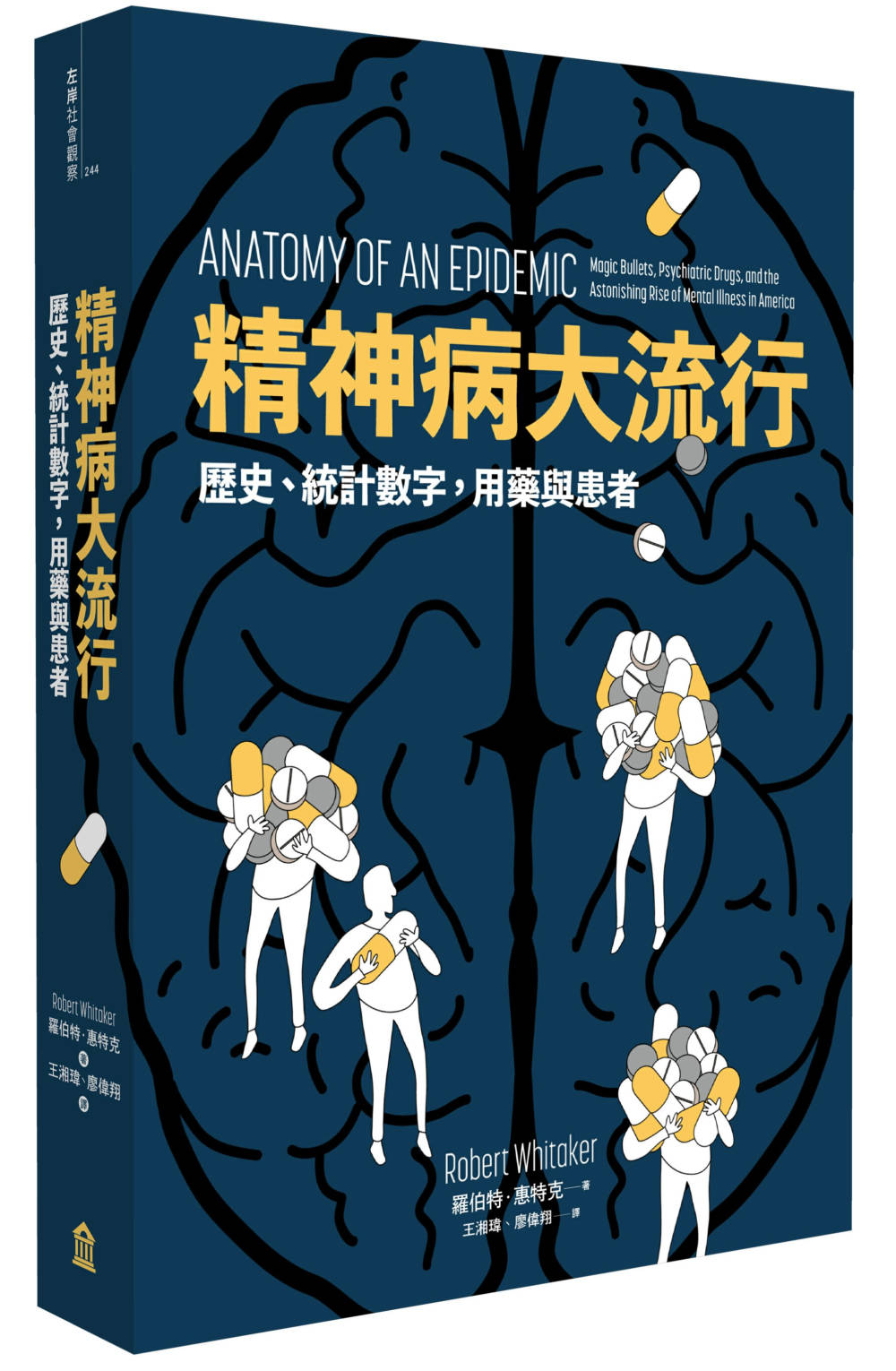
精神病大流行:歷史、統計數字,用藥與患者
你覺得精神疾病是生物學、心理學,還是社會關係的問題?
精神病究竟是存在於腦子裡、還是日常生活的相處之間?
「我可以想見將來有一天,精神醫學界的人會徹底遺忘我們的來路,忘記我們的起始之處是收容所,是濟貧院,是監獄。我可以想見將來有一天,我們會變成醫師,用醫師的方法思考精神病院的運作、院裡的醫病關係,和最好的內外科醫院差不了多少。」
精神醫學作為一門專科起始於19世紀的精神病院,只是當時的精神病院仍以收容、照護為主;19世紀末陸續開始出現高壓淋浴、藥物注射、睡眠療法等物理治療方式,不過仍與今日概念中的精神醫學相去甚遠。1930、1940年代,精神醫學界一度盛行「三合一」的治療方式:胰島素昏迷、電擊、額葉切除術。精神科醫師們開始直接對大腦下手,自此精神疾病的治療方式一路突飛猛進。二戰結束後,挾著戰時的醫學發展,1954年治療思覺失調症的藥物——「托拉靈」上市,精神藥物學時代正式展開;1988年「百憂解」出現,精神疾病治療再次大大地往前跨了一步。
不過,人們在精神方面的問題並未就此解決。
1955年,每468個美國人,就有一人因精神疾病而住院;到了1987年,每184個美國人,就有一人因精神疾病而失能,以致領取政府的失能補助。2007年,每76個美國人,就有一人因精神疾病而失能。從數字上,我們發現問題不太對勁;而這個問題也蔓延到兒童身上。過去二十年間,18歲以下的兒童、青少年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數是之前的三十五倍!
如果發明藥物是為了治癒疾病,為何精神科用藥發展的同時,卻使罹病的患者越來越多?會不會當代這種以藥物為主的醫療模式,反而引發了精神病大流行?
過去二十年來,精神醫學在一般人的觀念中有了相當大的轉變;我們不再「諱『疾』忌醫」,也開始接受藥物作為治療方式及其功效。1999年的精神醫學報告指稱,科學文獻的確證明了精神科用藥至少在「短期內」是「有效」的,有人說這些藥物就像「用來治療糖尿病的胰島素」;但長期而言,這些藥物真的「治療」了患者嗎?
本書從四個案例談起,接著講述精神疾病治療的歷史脈絡,以及藥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第三部分則是利用案例及研究資料,逐步探討近五十年來思覺失調症、焦慮症、憂鬱症、雙相情緒障礙症以及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在美國境內的盛行狀況,並針對每一種疾病的治療結果研究做了基本回顧。所以,是否我們自以為建立了一場精神醫療的革命,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第四部分的三個章節就是在討論這個問題。最後一部「解決之道」試圖從目前幾種發展中的解決方案,找出精神疾病另一種思考面向,以及其他可能的解方。
醫界如何看待用藥這件事?究竟什麼才是藥物真正的問題?這些藥物真的能幫助人們保持健康、生活得更好、擁有一個更健康的身體;還是正好相反,這些藥物使一個原本只是「暫時性的情緒危機」演變成「慢性精神疾病」?精神疾病患者是否必須終身用藥?
惠特克以「歷史」作為論述的主要武器。本書重新描述了精神醫學的歷史──只不過,說的是一個跟精神醫學主流敘事完全不同的故事。惠特克並借用當代精神醫學的遊戲規則:讓證據說話。書中大量引用精神醫學主流期刊的研究資料──只不過,是被官方歷史忽略的那些。此外,惠特克訪談近60個案例,呈現被目前精神醫學忽略的個人經驗。
惠特克試圖利用本書重新打開反思精神醫學論述空間,而本書正意味著,只要有足夠的歷史材料,總是蘊含著另一種敘說的可能性;一旦以不同的方式敘說,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就會隨之變化,而改變體制的可能性,就蘊含於其中。
作者簡介
羅伯特‧惠特克 Robert Whitaker
羅伯特‧惠特克為醫療科學報導作家,1992年曾於麻省理工學院擔任「奈特科學新聞研究員」(Knight Science Journalism fellow),其針對精神病患者及製藥工業的報導獲得多項醫學科學寫作獎項,如喬治‧波克獎(George Polk Award)。惠特克為《波士頓環球報》撰寫一系列關於精神病患被濫用藥物的報導曾獲1998年普立茲獎提名。
其他著作尚有《瘋狂美國》(Mad in America)、《地圖繪製者的妻子》(The Mapmaker's Wife)、《在上帝的膝上》(On the Laps of Gods),最新作品為2015年出版、與寇斯葛洛夫合著的《被影響的精神病學》(Psychiatry Under The Influence: Institutional Corruption, Social Injury, and Prescriptions for Reform)。
審訂者簡介
彭榮邦
不安於主流心理學的自我設限,有事沒事就撈過界的心理學家。進大學時主修化學,畢業時卻拿心理學文憑,碩士階段蹲點研究牽亡儀式,隨即踏入臨終照顧場域,最後以後殖民觀點的博士論文在美國杜肯大學取得了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他目前任教於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專長據說是現象學心理學,拉岡式精神分析,以及批判心理學史。
譯者簡介
王湘瑋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畢業,曾任職於出版社。
廖偉翔
成功大學醫學系畢業、政治系輔系。「公醫時代」創始成員,「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成員之一。合著有《島國關賤字》(左岸)。目前為北市聯醫仁愛院區不分科住院醫師。
導讀 打開潘朵拉之盒/彭榮邦
前言
第一部 解析一種流行病
第一章 現代瘟疫
精神病大流行/問一個科學的問題
第二章 軼事思考
四個故事/父母的兩難
第二部 精神科用藥的科學基礎
第三章 流行病的根源
設想一種新穎的精神醫學
第四章 精神醫學的神奇子彈
神經抑制劑、弱鎮定劑,與精神興奮劑/邪惡同盟/奇蹟藥丸/腦中的化學物質/達成期望/科學革命⋯⋯亦或社會妄想?
第五章 追獵化學失衡
接受考驗的血清素假說/多巴胺的舊事重演/理論的輓歌/百憂解,常在我心/一個理解精神藥物的模式/回到最初
第三部 治療成果
第六章 揭露一場悖論
思覺失調症的自然史/模糊的鏡中之影/抗精神病劑的例子/難題出現/比疾病更糟的治療?/超敏性精神病/這是個瘋狂的主意嗎?/臨床醫師的錯覺/證據回顧/凱希,喬治,和凱特
第七章 苯二氮平類藥物的圈套
眠爾通問世前的焦慮症/失寵的抗焦慮劑/苯二氮平類藥物的入門課/潔拉汀,海爾,和麗茲/失能者的數目
第八章 偶發疾病變成慢性病
憂鬱症從前的模樣/短期的藍色憂鬱/又是慢性因子/所有精神藥物都這樣運作嗎?/是疾病,而非藥物/未用藥v.s.用藥的憂鬱症/900萬,而且持續增加中/梅麗莎
第九章 雙相情緒障礙症大爆發
鋰鹽出現之前的雙相情緒障礙症/通往雙相情緒障礙症之路/鋰鹽的那些年/綜觀雙相情緒障礙症/已造成的傷害/圖表道盡了一切/雙相情緒障礙症的故事
第十章 解釋一場流行病
一個快速的思想實驗/解開一場謎團/身體疾病、認知損害,以及早死
第十一章 散布至兒童的流行病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興起/消極、坐著不動,以及孤單/慘遭淘汰的興奮劑/清點傷害/令人沮喪的結果/但又出現另一種疾病/創造雙相情緒障礙症兒童/等在前方的命運/失能者的數字
第十二章 受苦的孩子們
迷失於西雅圖/在雪城搖擺不定/如果你的監護者是國家,你一定有雙相情緒障礙症/回到雪城
第四部 細說一套妄想
第十三章 意識形態的興起
精神醫學的不滿之季/避重就輕/披上白袍/精神科的狂人/四部和聲/相信外星人的批評者
第十四章 人們所說的故事……以及沒說的
小謊,大謊,以及熱銷藥物/上場救援的山達基/遭愚弄的美國/《刺絡針》問了一個問題/抹除異議/隱藏證據
第十五章 清點獲利
一場商業上的勝利/搖錢樹/我們全都付了這筆帳
第五部 解決之道
第十六章 改革的藍圖
從一場絕食抗爭學到的教訓/一種精巧的照護形式/治療發生在「人與人之間」/天然的抗憂鬱劑/這些孩子棒極了/處於計畫階段/阿拉斯加計畫/我們人民
終章
誌謝
注釋
導讀
打開潘朵拉之盒
彭榮邦(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大概很少有一本書像這本一樣,〈前言〉幾乎就是一份清楚的「自我交代」。
本書作者羅伯特‧惠特克是位傑出的醫療記者,他為《波士頓環球報》所寫的系列醫療報導,曾經讓他和共筆的同事一起獲得1999年普立茲獎公共服務項目的提名殊榮。除此之外,他也是專門出版臨床試驗新知及媒合臨床試驗的全球性網路平台CenterWatch的合資老闆。在《精神病大流行》之前,他曾經寫過《瘋狂美國》一書(2002年初版,並於2010年再版),深入檢視了美國治療精神病患的歷史。照理來說,他應該相當有資格談論精神疾病的相關議題,不需要進行這麼多的「自我交代」,擔心讀者會誤解他寫這本書的意圖。
可就像惠特克在〈前言〉的一開始就明白指出的,精神醫學及其治療的歷史在美國社會是個相當具有爭議性的議題,或者說,是個很容易激化立場的「政治地雷區」。「自我交代」因此是他不得不穿上的防護衣。他必須告訴讀者,他不是別有所圖,也不是從一開始就質疑精神醫學的主流說法;甚至,以他身為出版社老闆的立場,或許不淌這趟渾水才是明智之舉。筆者自己也觀察到,過去幾年來在台灣精神醫療議題的公共討論的確也漸趨火爆。或許在這篇導讀的一開始,我們可以先簡單地考察一下,至少在歐美的部分,這個政治地雷區是如何成形的。
反精神醫學運動的起落
1960年代,對於長期受娛樂文化洗禮的讀者來說,最直接的聯想可能是「嬉皮」、「大麻」、「反戰」,或「搖滾樂」。這些浮面的印象沒有太大的差池,它們共同指向一種存在於當時歐美社會的「反文化」(counter culture)現象—對舊有體制不滿、甚至起身抵抗。在精神醫學界,1960年代也一樣動蕩不安,因為後來風起雲湧的所謂「反精神醫學」運動,也正是在當時那種「反叛」的時代氛圍之下成形。
提到「反精神醫學」運動,論者往往把它早期的發展和幾位重量級的學者及著作勾連在一起,例如: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連恩(R. D. Laing)的《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精神病院》(Asylums),以及薩斯(Thomas Szasz)的《精神疾病的神話》(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不約而同地,這些學者都對「精神疾病」是否可以被當作如同「身體疾病」一般的疾病實體來認識和治療,提出了來自不同思考方向的深刻質疑。
連恩認為,精神病患者的行為不一定非得被視為某種「疾病症狀的表現」,它也可以被視為患者「存在經驗的表達」。這意味著,精神病患者看似不合理的行為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我們懂得如何聆聽,我們就可以理解精神病患者的主體經驗,接近他們的世界。
傅柯在《精神疾病與心理學》(Maladie mentale et psychologie, 1962)時期的立場和連恩接近,也認為精神疾病和身體疾病有本質上的差異,不能以身體疾病的方式來認識,而必須從患者的存在經驗來加以掌握。可是到了《瘋癲與文明》,傅柯就遠離了存在現象學的立場,而是把精神疾病視為當代社會在理性化過程中,對「瘋狂」經驗的排除與禁閉。因此,「精神疾病」並非如物體一般實際存在,而是由精神醫學參與其中的、當代社會複雜權力知識關係所形構。
相對於傅柯宏觀的歷史論述,高夫曼的《精神病院》則是具體而微地從綿密的人際互動中,考察「精神疾病」是如何在精神病院這類全控機構內被模塑成形。高夫曼的考察發現,「精神疾病」的實體性是病患在自身社會網絡中被以特定方式標籤化(汙名)的結果。薩斯則在《精神疾病的神話》中明白地指陳,精神疾病不是發現,而是一種「發明」,它的圈圍和界定其實仰賴的是一套診斷標準,是被製造出來的「神話」,和身體疾病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這幾位重量級的學者,並不見得認同自己被歸類在所謂的「反精神醫學」的陣營(『反精神醫學』是後來才由南非精神分析師大衛‧古柏〔David Cooper〕給出的命名),傅柯及連恩即曾如此公開宣稱。他們之中,有些人確實積極參與了精神醫學體制的改造,例如高夫曼和薩斯,他們在廢除非志願性精神住院治療聯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薩斯的言論尤為辛辣,立場始終堅定,參與行動上也最積極,因此一直被視為美國「反精神醫學」運動的旗手,雖然薩斯覺得自己不是「反精神醫學」(anti-psychiatry),而是「反強制精神醫學」(anti-coercive psychiatry)。
在重量級學者的思想支援及反文化的時代氛圍支撐下,反精神醫學運動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對於促進歐美國家重視精神病患的人道照顧,例如精神病患照顧的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及社區精神醫療體系的建立,有重要的貢獻。然而,正因為反精神醫學的重要支援火力來自於其他的反文化團體,例如同志團體、女性團體或黑人團體,這些同盟力量的消散自然也成了反精神醫學運動的隱憂。
在反文化健將被學院吸收為明星教授、政治保守勢力重新盤點集結、經濟發展陷入停滯等因素下,反文化力量的形態由檯面轉入日常;反精神醫學運動也失去了從旁襄助的力量,在1980年代初期急速退溫。在英國,連恩及其同盟友愛兄弟協會在金斯利會所建立的實驗性治療社區難堪落幕,友愛兄弟協會也隨之分崩離析,反精神醫學運動幾近瓦解;而在美國,反精神醫學運動的發展則是隨著薩斯與山達基的合作,一步一步踏進了政治地雷區。
是合理批判,還是惡意毀謗?
山達基教會(The Church of Scientology)是由羅恩‧賀伯特(L. Ron Hubbard)於1950年代初期成立的新興宗教組織。它的組織龐大、信徒眾多,而且具有相當的政經實力,不過由於其行事上的爭議,在美國和不少國家都被視為異端。不管是從歷史恩怨(有些精神科醫師認為賀伯特有嚴重精神疾病)或是從教義(山達基認為精神醫學否定了人的靈性,提供錯誤的治療)來看,山達基對當代精神醫學的作為相當不認同,同時積極抵制。
姑且不論山達基的功過是非,但明白擺在眼前的是,這個宗教組織對許多人來說並不是正信宗教,如果需要取得公眾認同,與這個教會扯上關係絕非明智之舉。因此,薩斯和山達基的合作,對反精神醫學運動來說,就出現了額外的政治變數。薩斯本人在2009年的訪問中,提到他為什麼和山達基一起成立了「公民人權委員會」(Citize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他指出,不管是在當時還是現在,山達基是唯一一個有錢、有權、夠活躍,而且願意為精神病患的不當監禁付出的組織;雖然他並不相信其教義,但是他並不後悔自己和山達基合作。
問題是,如果考慮到批判主流精神醫學的論述空間,薩斯和山達基的合作,的確出現了削減論述能量和擠壓論述空間的後果。薩斯及其他反精神醫學運動倡議者的形象被極端化了,他們的著述因此失去應有的力道;批判精神醫學的論述空間也被激化了,進到這個場域發言的人很容易被貼標籤,也很容易用標籤對待發言立場不同的人。
重啟反思精神醫學的論述空間
惠特克在本書中就指出,山達基與反精神醫學運動的合流,表面上是主流精神醫學出現了強大的對手,但實際上卻是適得其反。山達基似乎在無意中成了主流精神醫學的「隊友」,讓他們得以輕鬆對付批判的力量;因為主流精神醫學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對手標籤為「山達基同路人」,根本無須正視其提出的論據。
從這個脈絡來看,惠特克的著作因此有了特別的意義:他想藉由《瘋狂美國》和《精神病大流行》,重新打開反思精神醫學的論述空間。惠特克在2010年為《瘋狂美國》再版所重寫的序言,和《精神病大流行》的序言類似,都有清楚「自我交代」的意味。這樣的自我交代,表面上看來像是自我保護,但從論述策略來看,卻是一種必要的「切割」,因為他想重起爐灶,再次開啟反思當代精神醫學的可能性。
在這個意義上,《瘋狂美國》和《精神病大流行》是姊妹之作,都是惠特克針對以生物醫學模式為主的當代精神醫學所做的重要批判。如果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惠特克首先是以「歷史」為其論述的主要武器。他在《瘋狂美國》2010年版的序言裡提到,這本書的副標題「糟糕的科學、糟糕的醫療,以及對精神病患的持續不當對待」(Bad Science, Bad Medicine, and the Enduring Mistreatment of the Mentally Ill)正是一個清楚的宣言,他想藉由這本書重述精神醫學的歷史,而且說的是一個跟精神醫學主流敘事完全不同的故事。
這個論述策略,對於已然被封閉的論述空間來說,有無比的重要性。任何一個體制的掌權者,都會對這個體制如何走到現在有一套官方說法,而這個官方版本的敘事往往是一種「成王敗寇」的歷史,凸顯了某些歷史事實(例如,為何是我當家作主),卻也遮蔽了另一些(例如,某些關鍵事件的發生只是歷史的偶然)。掌權者很在乎這個官方歷史,也會不斷地添加新事蹟,小心地維護著這個歷史,因為其權力的正當性就建立在這個歷史敘事之上。當代精神醫學的官方歷史所說的,幾乎就是一個生物精神醫學的進步史,而我們所有人,都因為生物醫學的進步受益。這個以生物醫學為主的歷史敘事,對精神醫學中的其他治療範式(例如精神分析),或其他文化的治療範式(例如台灣的牽亡儀式),或者以邊緣化或古董化的方式處理,或者根本就省略不提。
官方歷史本質上是一種維護體制的歷史,如果我們接受了這樣的歷史視野,我們就很難跳出體制的意識形態框架,想像出其他的可能性,即使當前的體制已經陷入危機。幸運的是,真正的歷史—事件因為各種可能性條件的因緣聚合而浮現或隱沒—其實並不是這麼「乾淨」地線性開展,而是充滿著衝突、斷裂和替代的動態過程。這意味著,只要有足夠的歷史材料,它總是蘊含著另一種敘說的可能性,一旦以不同的方式敘說,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就會隨之變化,而改變體制的可能性就蘊含於其中。
接續《瘋狂美國》對當代精神醫學主流歷史敘事的鬆動,惠特克在《精神病大流行》更使用了另一個或許讓某些人恨得牙癢癢的論述策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當代精神醫學強調實證研究的「讓證據說話」,然而,不管在實證研究的方法或證據的解釋上,卻不時出現選擇性強調或是有意無意的疏漏。因此,惠特克特別強調,他不僅願意接受實證研究「讓證據說話」的遊戲規則,而且他用來佐證論述的資料,幾乎都出自精神醫學的主流期刊。只不過,他問的可能是當前研究範式不常提出或試圖迴避的問題(例如,服用某種精神藥物的長期成效),他所累積的論述證據和觀察,可能來自目前精神醫學忽略、甚至視而不見的研究或個人經驗。
台灣:美國主流精神醫學全球化的現場
1950年代之後的「精神藥理學革命」影響的不只是美國,而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特別在1980年代之後,《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和精神藥物治療模式,幾乎是以肩並肩的方式,快速擴張到全球各地。雖然著名的精神科醫師及醫療人類學家凱博文(Arthur Kleinman)早在1988年的著作《反思精神醫學》(Rethinking Psychiatry)中就指出,我們必須正視為什麼占了全世界80%人口的非西方社會,必須沿用一套深植於歐美文化的精神醫療模式,但是他與同事們的研究成果,並沒有太大地撼動精神醫學的生物醫學模式。
讓我們暫且擱置對精神疾病生物性的爭議,任何一種所謂的「精神疾病」,它都有疾病診斷道不盡、甚至忽略的主體經驗,而且是由精神醫學參與其中的複雜權力知識關係,和病人日常生活的綿密人際互動所形構。換句話說,「精神疾病」的實體性,其實是一種鑲嵌於特定時空、社會文化的整體布署,牽一髮而全身動,我們在惠特克的歷史敘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筆者認為,這也是凱博文多年來提倡精神醫學的「生物心理社會模式」(biopsychosocial)的深刻意涵。
如果真是如此,那麼美國主流精神醫學的全球化,就成了一件相當可疑的事情,因為它的整體布署,很難拆解輸出而不改變本質。「精神疾病診斷」及「藥物治療」是最容易跨國輸出的部分,但是構成「精神疾病」整體布署的其他向度,例如社會福利、特殊教育,以及其他接應精神病患的體制和人際網絡,恐怕就很難跨越國界,或至少在速度上遠遠落後。更需要注意的是,這個只有「部分輸出」的精神醫學,很可能改變或遮蔽了某些正在醞釀中的歷史過程。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的診斷及藥物治療在台灣所引起的激辯,我們或許可以試著這麼理解。即使精神科醫師懷著最大的善意給予治療,但因為這個「精神疾病」的整體布署只有部分輸出,原本對病人較為全面性的接應,到頭來只剩下藥物治療。結果是,精神科醫師越努力,整體偏斜越嚴重,可能引發的爭議就越多。不僅如此,部分學童在課堂上的「注意力不集中」或「坐不住」,可能和台灣社會正在經歷的快速變動有關。ADHD的質疑往往是由學校老師發動,而這其中有多少複雜問題是被單純地「醫療化」,筆者心中一直存有疑問。
雖然閱讀這本書的過程,有如打開精神醫學的潘朵拉盒子,但對於台灣目前過度一面倒的精神醫學資訊,這本書的出版絕對可以產生重要的平衡效果。
第二章 軼事思考 若我們看重求知的歷程,便該自由地追隨這樣的歷程,無論它將帶領我們前往何處。—艾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 1952) 美國麻州伯蒙特的麥克林醫院(McLean Hospital)是間歷史相當悠久的精神科醫院,1987年創立,當時貴格會信徒正在提倡「人道療法」(moral therapy)的照護方式。他們相信為精神病患者設置的休養所應該要充滿田園氣息,所以即使到了今天,麥克林院區給人的感覺仍然像個綠洲,磚屋韻味十足、草坪樹影婆娑。2008年8月某天晚上,我來到麥克林參加一場聚會,主辦單位是憂鬱症雙相情緒障礙症支援聯盟(Depression and Bipolar Support Alliance, DBSA,以下簡稱「憂雙盟」);當時的天氣格外讓人感覺靜謐。那晚真是最美好的夏夜,走向醫院餐廳的路上,我暗自猜想,今晚來的人大概很少吧,如此宜人的夜晚,怎麼捨得待在室內。這是社區居民的聚會,也就是說,他們必須離開自個兒家裡,特地來到這兒;既然麥克林的支援團體每週聚會五次(週一、四、五、六下午各一次,週三晚上一次),我猜他們多半會略過這次聚會。 我錯了。 醫院餐廳擠進了百來人,而這場景約略也說明了美國二十年來精神失能流行之烈。憂雙盟成立於1985年(舊稱憂鬱症躁鬱症協會,Depressive and Manic-Depressive Association),麥克林的支援團體也在不久之後開始運作,目前該組織在全美國有近千個支援團體,光是大波士頓地區就有七個;這些支援團體大部分是讓民眾每星期有幾次聚在一起談話的機會(麥克林的支援團體亦然)。隨著精神疾病的流行,憂雙盟也一步步成長。 聚會的第一個小時是關於「漂浮舒緩療法」的演講,而底下聽眾給人的第一印象完全不像是病人(至少我這種外人一點都看不出來)。這群人年齡分布甚廣,最小的不到20歲,最長的則有60多歲;女多於男,但這種性別差異可以想見,憂鬱症的女性患者本就多於男性患者;大部分是白人,這也許是因為伯蒙特是一個相當富裕的城鎮。只有一個清楚的跡象顯示出這可能是一場精神病患者的聚會,那就是許多與會者體重過重。醫師通常會開給雙相情緒障礙症患者非典型抗精神病劑,例如金普薩(Zyprexa),而這類藥物往往會使人多個好幾公斤。
 大偽裝者:一個臥底精神病院的心理學...
大偽裝者:一個臥底精神病院的心理學...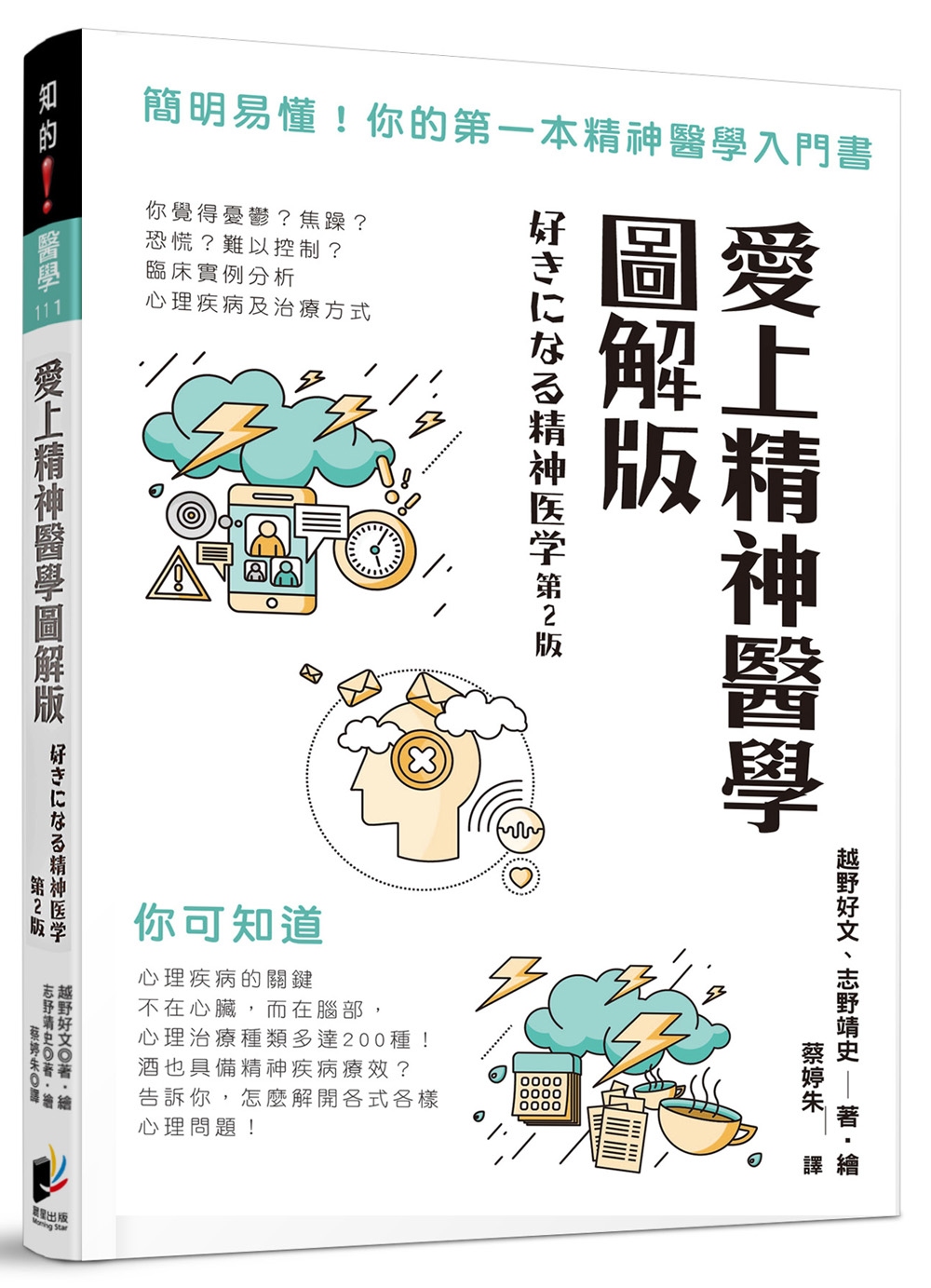 愛上精神醫學圖解版:簡明易懂!你的...
愛上精神醫學圖解版:簡明易懂!你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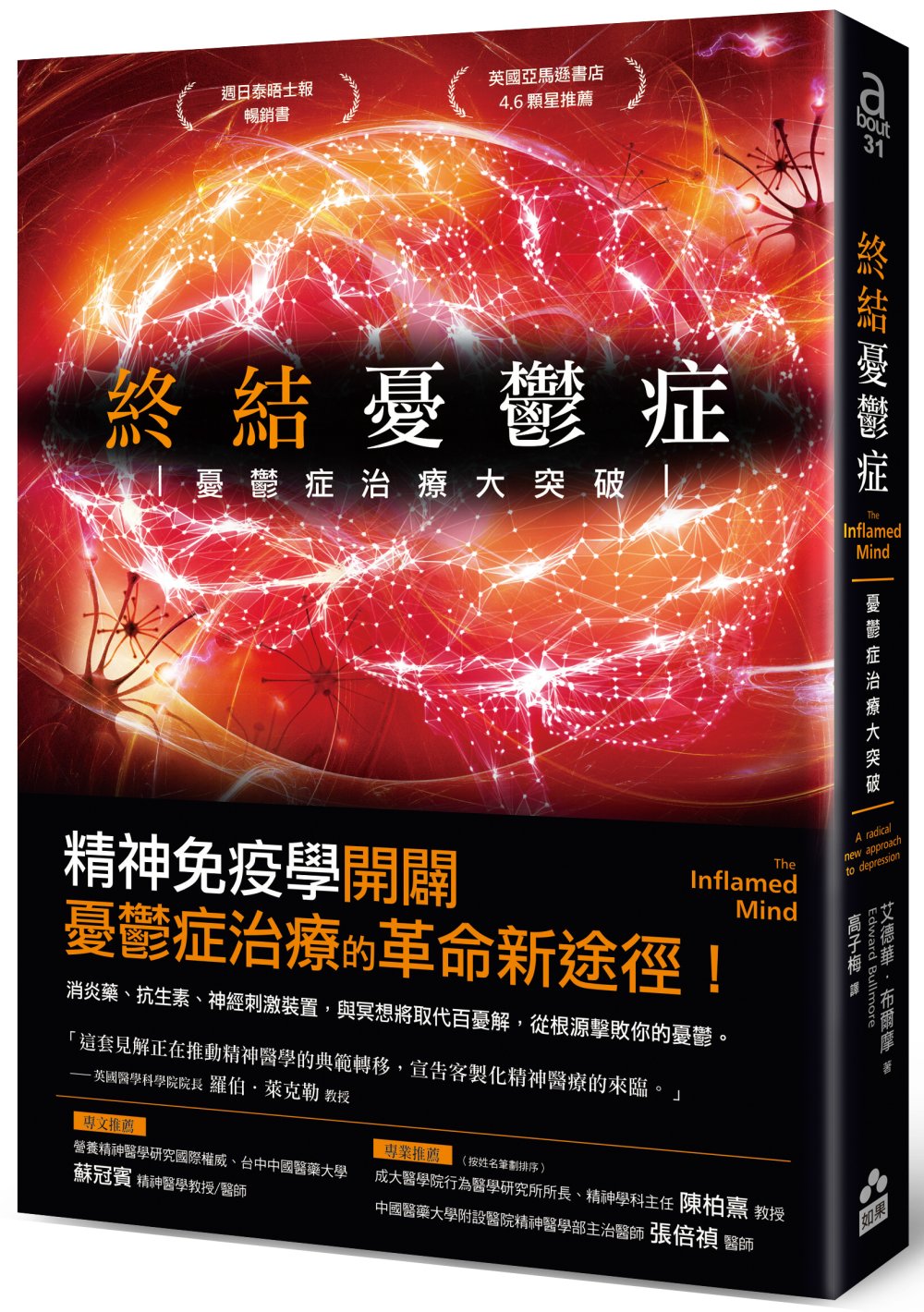 終結憂鬱症:憂鬱症治療大突破
終結憂鬱症:憂鬱症治療大突破 我們都有病:逃避,有什麼關係?致為...
我們都有病:逃避,有什麼關係?致為... 陪伴孩子的情緒行為障礙
陪伴孩子的情緒行為障礙 走過愛的蠻荒:撕掉羞恥印記,與溫柔...
走過愛的蠻荒:撕掉羞恥印記,與溫柔...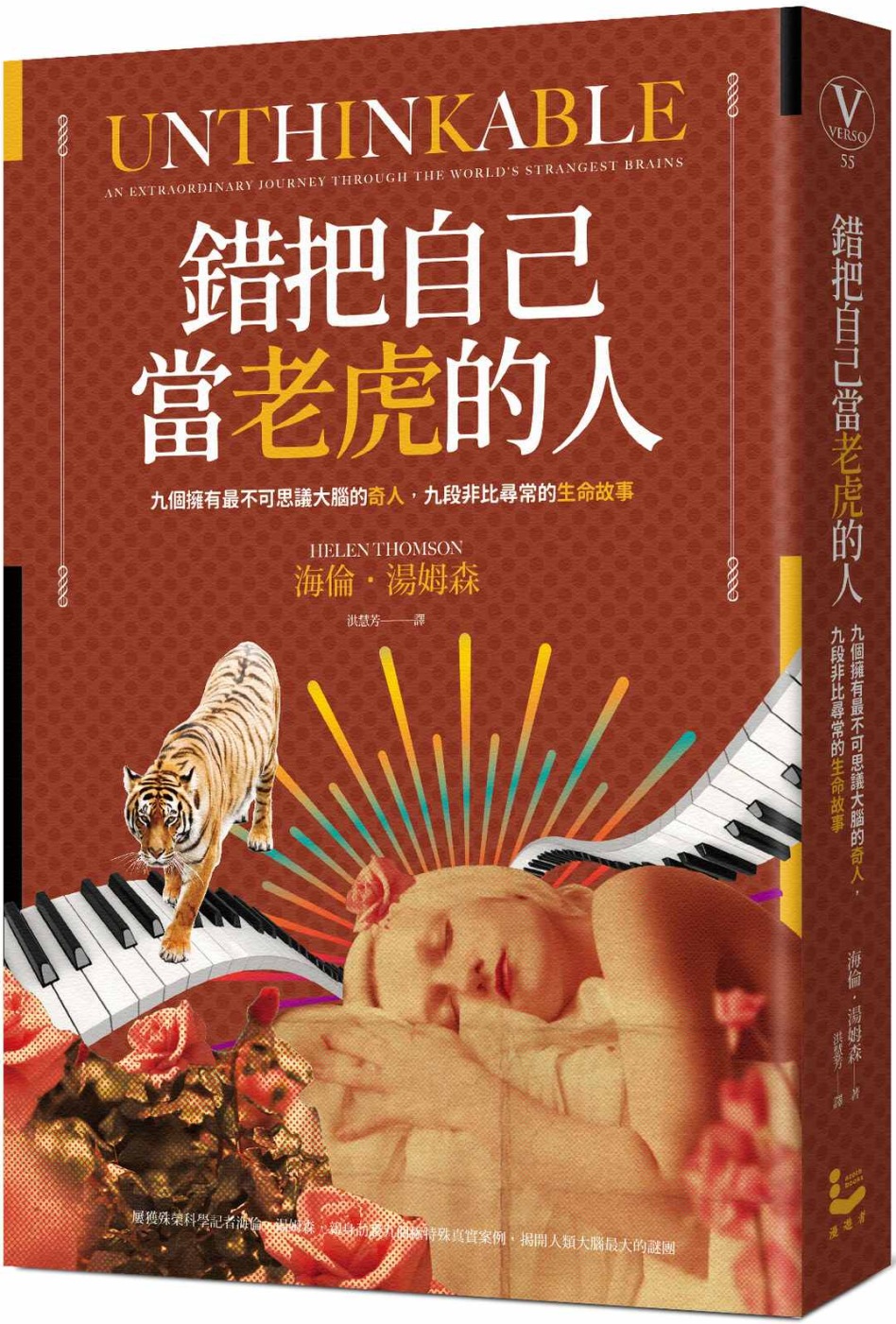 錯把自己當老虎的人:九個擁有最不可...
錯把自己當老虎的人:九個擁有最不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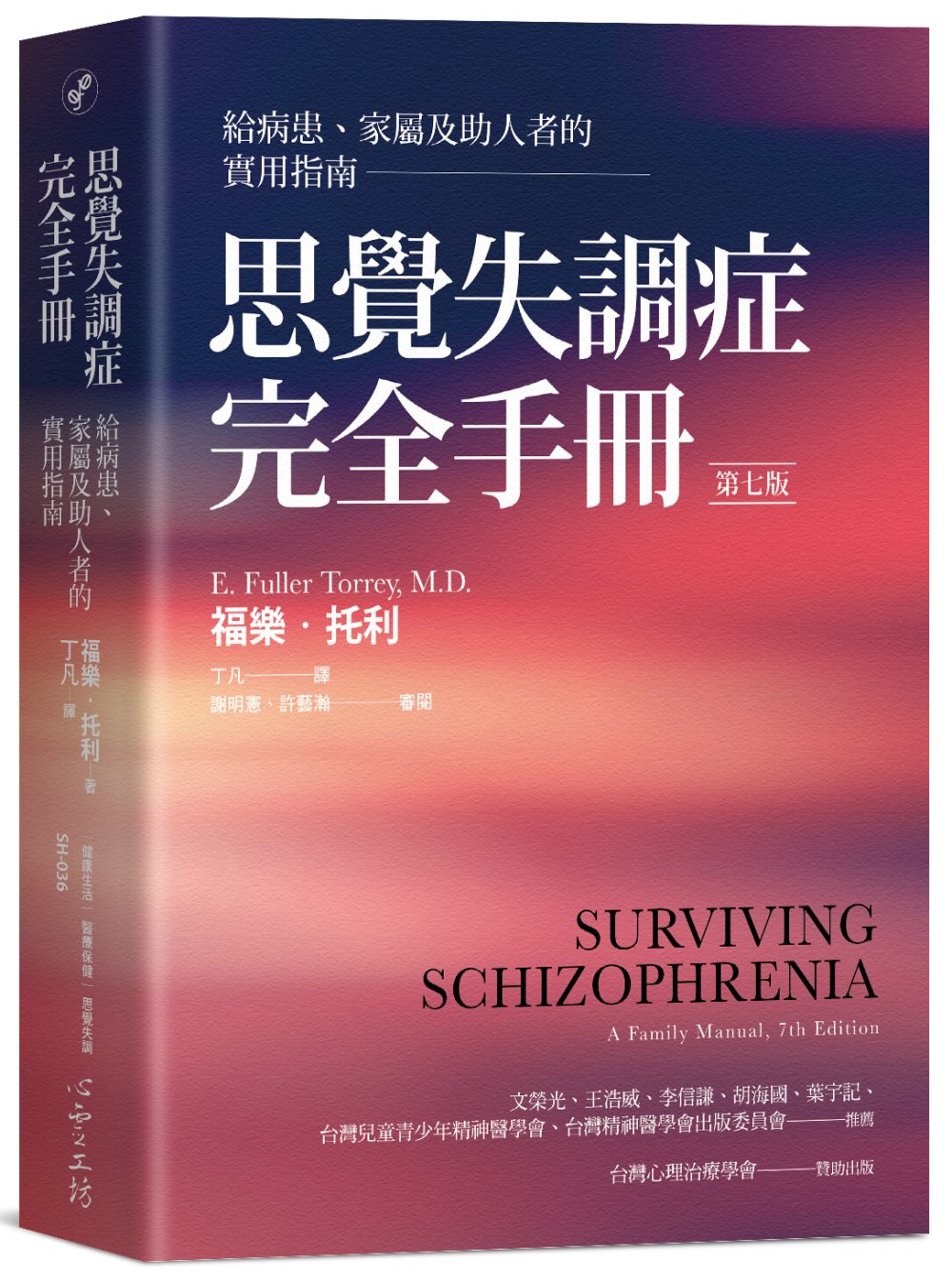 思覺失調症完全手冊:給病患、家屬及...
思覺失調症完全手冊:給病患、家屬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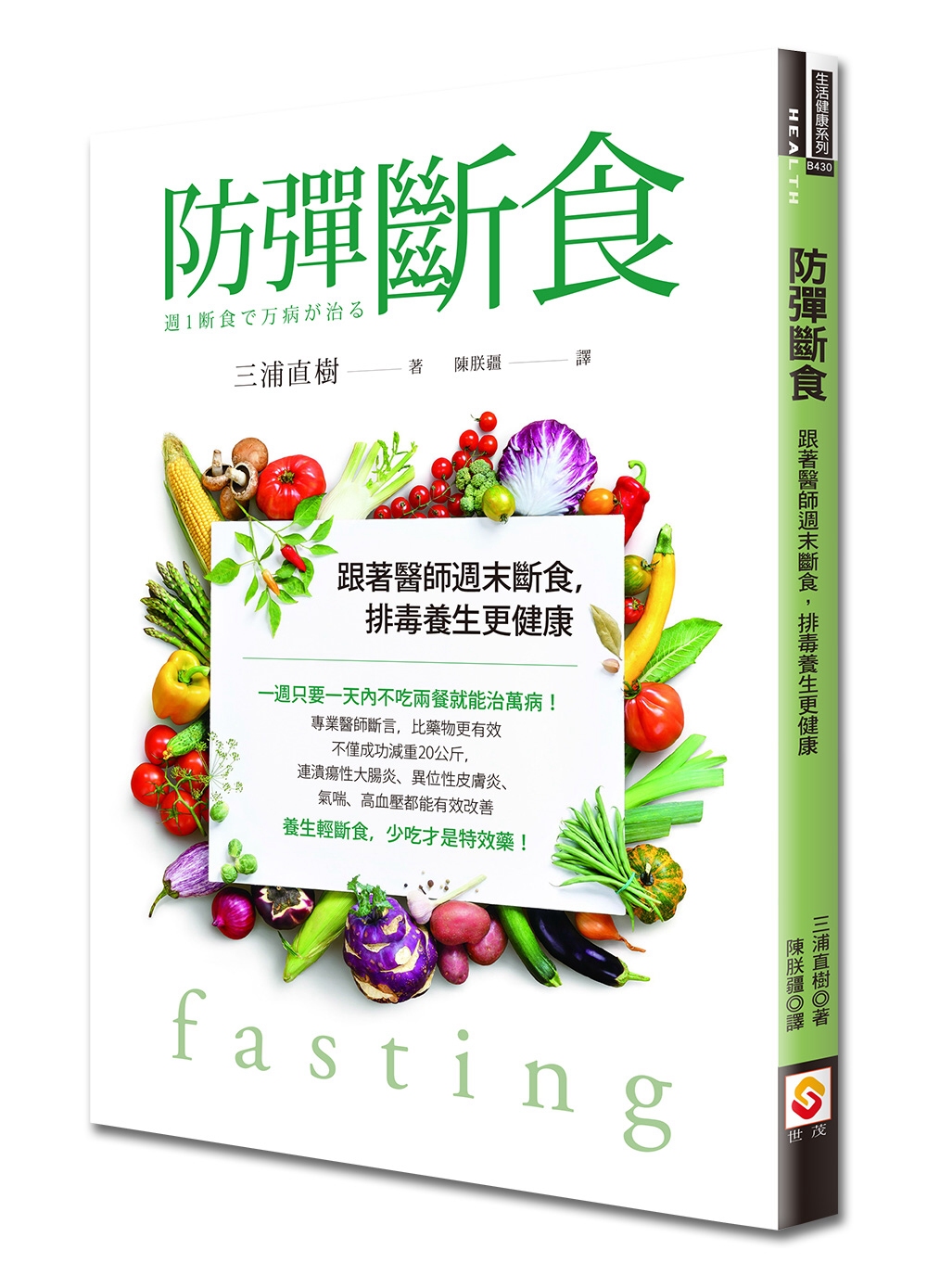 防彈斷食:跟著醫師週末斷食,排毒養...
防彈斷食:跟著醫師週末斷食,排毒養... 生酮治病飲食全書:酮體自救飲食者最...
生酮治病飲食全書:酮體自救飲食者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