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就不喜歡魯迅:從政治異見到文化異見 | 生病了怎麼辦 - 2024年5月

我從來就不喜歡魯迅:從政治異見到文化異見
思想宣佈禁欲它怕酒後失態降低了自己的價值不過,它那撲鼻的口臭勝過了難聞的酒氣!
自由.理性.神學.性與慾──異議人士的異議思維,思考無邊界!
「暴力加謊言,是一切與自由為敵的無知兼無恥的勢力們的鎮宅之寶。」
中國知名異議人士綦彥臣,力倡獨立思想的重要性,透過對自由、理性、神學甚至性慾的等議題的深入探討,提出與眾不同的見解--不受權力控制,擺脫道德約束,「即便你把我關在籠子裡,四周蒙上黑布,我還總有自慰的自由。我願意想誰,就想誰。」這,就是思想自由的精神!
本書特色
不受權力控制,擺脫道德約束--中國異議人士綦彥臣提出對於政治和文化的獨家見解!
作者簡介
綦彥臣
作家,獨立中文筆會成員,中國知名異議人士,網易歷史名博「半個歷史學家」博主。著有長篇小說《絕育:一個死囚的微觀大歷史》(秀威出版,2013.02)。經濟暨時政評論文章常見於香港《爭鳴》與《動向》雜誌,現為美國中文網刊《民主中國》排名第一的專欄作者。
自序 政治往事與這本書
【第一輯 心境.閑趣】論自由關於自由的小故事閒靜之時修舊書幸福與責任並不對立幸福是可以揮霍的至樂之魚,似曾相識的東西方文明當時代有愧於一些人的時候神一百的時代,有否可能?性、恩怨以及情人節的「人情化」不妨測量一下自己的性品位致屌絲:窮人要尊重自己的出身魯迅的西學缺憾--阿Q畫圈的另一種詮釋我從來就不喜歡魯迅狗權邊界:人的動物性會經常暴露級別,官本位,懷才之遇與「不遇」
【第二輯 沉思.洞見】哈佛想像,「哈狗幫」與諾獎學外語不單單是為了學技能幸福的重要內容之一是伺候兒女警惕學校裡的軟暴力--我為什麼幫女兒對抗老師學會拒絕語放棄,才有幸福軟背景─理解我們這個世界的最關鍵因素人性最醜陋一面往往由良言表現遠離大眾法西斯--警惕那些不是「好人家兒出來的」人一張可作為傳家寶的照片昂藏老鶴風--茅于軾評傳簡單的愛,含有深刻的道理超級理性,是無盡的快樂裝蛋與裝聖真他媽少一竅,德里達會這樣罵人嗎?我所理解的交往理性有宗教而無神學的危險懂得服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清華的進步:從棍子到文書「鳳姐」的隱私部位比「維清派」的腦子乾淨看官,你得這樣「看官」業務員水平的一代人、一個類型的人李從軍的「鞋說」,克宮之學的「經典」性罰的正當性問題--「打飛機」服務為什麼不應入罪?政府永遠不會比市場聰明
【第三輯 書影.觀點】公平何以在信仰之上?--《信仰的力量》一書讀後親情與信仰能否平衡--《信仰的力量》一書讀後(續)為流亡者的思想描點--蔡楚詩選《別夢成灰》淺讀「白封出版」的重大意義--推薦好書《思想的蝴蝶》丁朗父的薩米亞特情結--詩集《穿過這寒霧我的弟兄們》品讀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閒話Samuelson漢譯名議會打架是件大好事--從美國到臺灣的「潛流」非祭而賀蘇共亡黨二十年--對《克格勃全史》的拓展閱讀雜果佐酒待有時--略讀宮鈴《從臺北到北京》偶感一句話的價值--推薦弗雷德曼夫婦著《兩個幸福的人》梭羅是誰?有中國映射嗎?--初讀《瓦爾登湖》有感對阿貝拉爾的借題發揮--電影《達.文西密碼》歷史趣解域外聊齋裡的父女--電影《暮光之城》觀略那麼體面,何以沒有上帝?--電影《驚懼黑皮書》沉思克莉絲塔與魯迅何干?--電影《竊聽風暴》裡的體制恐懼
後記 安享靈性的寧靜、愉悅與豐滿
序
作為大陸的一位民間經濟學家、通俗歷史寫手,特別曾坐過政治牢獄的異見人士,我心儀臺灣已久,儘管我未曾去過臺灣。說起與臺灣的淵源來,最遠可以追溯到我少年時代「拾傳單」的經歷-一九七○年代,國共仍然隔岸對抗,常有傳單隨季風飄來(遠至我家鄉所在的華北平原),小學裡就動員我們那些在校學生去田裡搜尋。
和「臺灣」這個在大陸充滿政治含義的辭彙相聯繫,以至於影響命運的因素至今仍在,起源於一樁政治案件。一九九九年九月二日,我被河北省滄州市國家安全局刑事拘留,經過十三個月的羈押,最後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四年徒刑。案件中有兩處涉及臺灣:第一,一九九九年五月,「向『中華民國』僑委會主辦的反動徵文比賽投寄文章〈臺灣的貢獻與非主流統派論〉,讚頌臺灣的所謂『民主』,吹捧臺灣國民黨政權,造謠惑眾,汙衊共產黨政權,鼓動群眾推翻共產黨,以臺灣『民主』為模式,實行多黨制。此文被採用發表,綦得稿費二一○○元台幣。」;第二,一九九九年八月,「將自己撰寫的稿件〈中國的崩潰與未來重建〉向臺灣遠景基金會暨《遠景學刊》投送,同時與美國反動電子刊物《小參考》聯繫出版事宜,還為此向香港《開放》雜誌社尋求過出版資助。
該稿件包括〈前言:為了一個簡單的事實〉、〈上卷導論:『崩潰』的概念〉、〈下卷導論:重建工作的重點〉、〈下卷第一章 民主並不完美:針對歷史文化沉澱的真實話語〉等文章,整個文稿汙衊人民民主專政是『暴政』,號召『組織黨派、籌集經費、舉行抗議』,顛覆國家政權,實現資本主義『自由、民主、憲政』政治體制。」
法律層面的東西有文書在,相信有朝一日會有更多的事實披露出來,比如為何給僑委會寫文章被最後判為有罪,而給遠景基金會寫文章沒有被判罪。按大陸辦理政治案件的規定,不管文章是否最後發表,只要寄出(交給郵局或從網路發出)就算行為實施。對此,我不願再費心探討,倒是在我被抓後傳出的謠言讓我頗費思量。謠言到我出獄後還在流傳,說是我有一台發報機被國家安全機關查獲,查獲前我已經給臺灣國民黨發了大量的情報。
我姐姐在我被羈押時,到處打聽我犯了什麼罪,一位自稱是我中專時代同學的滄州檢察機關幹部說:「你兄弟要跟國民黨聯手。國民黨回來,他當總統。」姐姐是個農村婦女,很善良,小學文化,一聽這話,就暈了。直到我被送石家莊北郊監獄(省四監)並能會見近親屬了,才知道我沒給臺灣「發報」,也沒想「當總統」的意思。我想,說我給臺灣發報是個陰謀。彼時,大陸人們有個習慣性思維,你不愛黨可以,不愛國就是罪惡。
現在,這種思維淡化多了,蓋因貧富差距刺激之故。陰謀的發起者給我編上向臺灣發報的情節,我就貼近賣國了。配合這個陰謀,新華社辦的《內參選編》(簡稱《內參》)也發文說我非法獲取國家秘密(原文無法見到,因此刊是國家秘密級的)。我的內弟在郵局工作,他們局裡的人在我被抓後告訴他:「你大姐夫的事兒上《內參》了。」內弟是個謹小慎微的人,私下告訴他大姐:「你家的事兒都上《內參》了。大了!」
再後來,我出獄(二○○三年五月一日提前四個月獲釋,源於國際社會不斷交涉之故)幾年後,打羽毛球鍛煉身體(二○○七年十二月開始),有一位球友在涉密部門工作過,在一次宴會(大陸俗稱「飯局」)私聊時,問我:「你這麼聰明的人怎麼會幹那事兒?後悔不?」我知道該人士說的是洩密暨「發報」那些事情,我告訴對方:「我的罪名只有一項,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沒有非法獲取國家秘密。」其人釋然。這位球友的發問絕非偶然,而是我們小城市裡有點級別的公務人員的共同疑惑。同樣是副科級別(這個級別在小城市已經是「大官」了)的另一位熟人,也在某次私人飯局上問過我「洩密」的原因。時隔多年,平靜回顧當初,可以說民間版本的我給臺灣「發報」也不是一點「根據」都沒有。我早在一九九二年就有一部手動英文打字機,這在一個四線城市(縣級市)是個奇蹟,其實我是用它來寫英文小稿的(那時還沒文祕辦公電腦),單位的上司堅持說那是發報機(手動打字機不用電,怎麼能發報呢?)。
有發報機給哪裡發報呢,人們一想就是臺灣。再加上官場向外流傳的資訊,事情就「更像真事兒」了。國安局的《起訴意見書》上也確實指控我兩項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與非法獲取國家秘密,檢察院的《起訴書》列了這兩項,但最後要求法院判決的是一項即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至於國安局的指控根據,則是我家裡(書房)放有三份《內參》,按級別我作為副股級科員(當過銀行營業所主管信貸的副主任)無權看這個秘密級的東西,只有我們單位的一把手(行長,正科局級,相當於一個鎮的鎮長的級別)才有權看。但是,我作為工作在一線的學者經常為北京總行承擔課題,看《內參》可以摸清上邊思路再來結合課題,單位也特許我看。我想,沒有形成最終指控的一個最大可能是我有權看上海市政府辦的秘密級內刊《經濟預測》。
這個內刊約我寫稿,除了正常稿費,每月還給五百元人民幣資訊費。上海市政府跟《內參》的主辦者新華社至少平級,我因學術原因看了同級秘密,很可能抵消了私存《內參》的「罪過」。未經證實的說法是,《經濟預測》發到正處級(相當於一個縣的縣長的級別),也有說發到正廳級的。簡單地說,不管發到哪個級別,總不比我們單位(銀行)的級別要低。儘管未經證實,它上面印的「領導參閱,妥善保存」足以說明作為它的贈刊對象,我有資格看到秘密級別的東西。同理,看《內參》也不成為問題。或者說,在國家秘密問題上,我比我們科局級的行長高一檔兩級。大陸的官本位就這麼奇怪。
我也知道領導一直嫉妒我,比如扣押上海方面給我的資訊費匯款單,私下問是不是臺灣方面經上海轉來的。還有,負責監督我政治行為的同事在我不知情也即沒允許的情況下,拆開我的雜誌郵件,不管是上海來的,還是香港來的,還是臺灣來的。我要質問,對方就說:「反正都是雜誌,又不是寫的信。」
我無意於深責那些參與監督我的當年領導、同事,但是,對於他們在我出獄後絲毫沒有歉意,很是驚詫。驚詫之餘,只能以「黨性高於人性」來詮釋。還有,按國家法律,公民有向國家司法機關作證的義務。這點我不能怪。但是,你總不能為了作證而不尊重我的人格而採取非法手段。未經你的同意,就拆開你的郵件,你是什麼感覺?
關於政治案件的老黃曆,不再多說。而究竟內幕如何,有待以後的歷史揭秘。
造謠我給臺灣「發報」雖然是個陰謀,是個汙衊,但是並沒有影響我對臺灣的嚮往。在出獄後,做「文化個體戶」或叫獨立學者的生涯中,我有許多文章涉及到臺灣,文化感悟的、學術的,都有。比如,我翻譯過一本英文書,是女性南極探險的自述。那個事情很轟動,臺灣用這個事情做大地震後重建的勵志案例,鼓勵人們克服困難;而大陸這邊沒有任何媒體提及這個事情,直到我在二○○三年下半年我給書商(半合法的民間代理,俗稱「二渠道」)翻譯那本探險書時,才知道有這麼個事情,由此感觸兩岸在文化上是漸行漸遠了。
此種感觸並非僅僅來自對臺灣民主制度的讚賞暨感情,更來自對臺灣本土人士的接觸。記得一九九八年秋天,我隨朋友在北京與一位臺灣記者見面,我自以為發表過兩岸農業金融制度的比較論文,就能「說說臺灣」,但當對方問我「你知道臺灣兩千多萬人的感受嗎」時,我有些尷尬。由此,渴望瞭解臺灣就成了一大心結,以至於冒險給臺灣報刊投稿。
出獄後,環境已經有些變化,在微妙亦不確定的環境裡,我接觸到臺灣政界人士,原因是鳳凰衛視在北京錄節目,請我去做場外嘉賓,就是在觀眾席上能發言的人,討論臺灣大選問題。當時,臺灣的親民黨、民進黨、國民黨選戰頗酣,新黨雖未參選,但也不斷發聲。看看國民黨的人、親民黨的人、還有新黨人在北京說什麼還是不錯的,所以,我答應了邀請,儘管作為民間「大牌」學者坐在觀眾席上有些「委屈」。
我不知道鳳凰衛視的工作人員為何邀請我,私下裡想可能是我在境外電子媒體上老寫關於臺灣政治的文章之故,他們也看得見。比如,作為美國中文電子雜誌《民主中國》排名第一的專欄作者,我有一個政治學與戰略學合成的學術系列「中國民主化外部因素之戰略學解析」,其中分析臺灣作用頗受外界關注。
不管是什麼原因,我去了。節目散後,我和國民黨的一位高層黨務人士(也是臺北市議員,李彥秀女士)交換了名片,還與自稱「胡同台妹」的臺灣媒體駐京記者宮鈴談了一會兒。後來,見到宮鈴的書在大陸出版了,買了一本,讀後主動寫了書評。不用說太樸素的感情話語,但臺灣政治人物給大陸學者們的感覺確實是親切的。我這樣的異議分子不用說了,就是在大陸體制內做得相當成功的人士,要見中共黨務高層人士並交換名片,恐怕是很難事情。還有,宮鈴的書給了我們很多現實的細節,讓我們看到大陸和臺灣在文化方面的差異,所以,我寫給她寫書評完全出於自願,也不圖她日後幫助什麼?當時(節目散後),沒和她交換名片。
按著正常的商業途徑在臺灣出版自己的著作,是我老早以來的願望,比如十三年前與臺灣遠景基金會聯繫《中國的崩潰與未來重建》一書的出版事宜(那本書稿沒有完成,國安局抄走後,在案件了結時直至今日也沒退還)。近年來,國內環境雖有較大鬆動,但是,明裡暗裡的限制還是很多的,尤其以商業面目出現的限制,可視為當局統治策略的調整。手頭已經完成,甚至存了十年書出不了的有之,比如一本在監獄時寫完的小說《絕育》,無法在大陸出版。
甚至有一家播音網站已經訂好要播,後來懼於當局的查辦而取消合作。為何敏感,就是那本小說描寫了共產黨革命時代好殺成性的細節以及後來「文革」中的骯髒人性。與「文革」題材的敏感性相關,我寫的另一本書《人隨社會草隨風》也出版不了。後來,我不得不把全書拆開,改名為《我的「文革」記憶》,陸續發在自己的博客上。去年一年,官方推開所謂文化體制改革以前,對我的控制明顯強化,一本歷史書《給歷史放把火》經歷一年多的審稿才勉強出了。到今年初,其實我已經打算放棄在大陸出書的努力,儘管有的出版代理人試圖把過來我的版權到期著作整合成文集。有書出不了,又不是質量(市場前景)問題,不能不說是對作家的侮辱!
承受侮辱也不僅僅是有書出不了,就是能出版的,不經過出版社的蠻橫刪削,也是出不成的,且不論給你多少錢。有時,出版社甚至是整章給你刪掉。
比如,二○○九年在新華出版社出的《乾隆爺那些事兒裡筆記野史中的南巡故事》,被拿掉關於乾隆佞佛的一整章。問其故,有人私下回曰:「佛教正在國教化,譏笑乾隆佞佛,版署會卡死。」歷史閒篇,如此對待也就罷了,連非常有學術品位的經濟學作品也無法倖免。《真實的交易裡提高生活質量的通俗經濟學》是遭遇最嚴重刪削的一本。被刪掉的獨立小節有四個,共計七千六百字;被刪掉小節內含部分一處,二千一百字;被刪掉的整章一個,計有一萬三千字。原來十五萬字,最適合讀者通俗閱讀的情狀,被刪掉兩萬多字,以至於沒法保證著作思想的系統性。但我沒辦法,出版代理合同上寫著對方有刪節權。作家不同意行嗎?要麼,別出。
然而,天無絕人之路,藉助互聯網的國際交流功能,我應邀與英籍華裔作家高安華女士在網易微博上,又經高女士介紹和臺灣秀威出版公司(showwe)建立了聯繫,在大陸近十年不得出版的小說《絕育》由秀威出版,而且是無刪節本。對於一個以異見身份生存於大陸的學者、作家來說,該是何等的興奮!此非誇張,我想臺灣經歷戡亂與解嚴之轉變,至今仍然健在且有過異議經歷的人,在解嚴前能在香港或北美出一本自己的書,應是與我同樣的感覺,儘管他們的經歷已經成為歷史,而我正經歷著歷史。
在小說《絕育》出版合同簽完之後,我就打算在秀威繼續出書,並做了系列選題。這本書就是日間陸續發在網易博客上的博文的精選,其中大部分被網易博客做過首頁推薦。計畫已定,就是自己進行初步編輯的工作。
從我二○○三年五月出獄以來,當局就擔心我會「叛逃」。我明言相告:「即便是走,我也會堂堂正正地走,向你們申請。絕不會以雞鳴狗盜的方式溜走!批不批准我走是你們的事情,反正在國內我也是做『流亡』的。」當然,這裡我沒有諷刺那些出於無奈而選擇了「叛逃」的異議者們,並且按著美國著名大法官路易士.布蘭代斯關於自由的說法,一個人選擇何種自由途徑無須他人指點。哈耶克在《自由憲章》一書裡也引述了這個說法。儘管我說不會「叛逃」,當局還是不相信,以至於在某個敏感期有我的某位鄰居(警員)在我不知情的前提下,向他上級的上級擔保我不會越境出逃。
事後,這位鄰居給我打來電話,詳盡解釋。我呢,哭笑不得,也無法責怪此人。但是,我在電話裡告訴他一個我的打算:「你們要放我走,我就去臺灣。但是,我不知道手續怎麼辦,或者定居臺灣算不算『移民』。」對方說問題太複雜,沒法電話裡跟我說清楚,等請示上級以後再說。鄰居「請示」上級已經六七年的時間了,也沒答覆我。我呢,「移民」臺灣的打算還是如初之堅。不管「移民」臺灣的打算是否能夠付諸實際,我心儀臺灣的個人心境是不可能改變的。
說到本書的立意之一是紀念帕斯捷爾納克,就不得不比較他的《日瓦戈醫生》與我的《絕育》兩部小說的相似遭遇。前蘇聯時代,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日瓦戈醫生》寫了十年,完成後難以出版,若出版就得接受出版管控當局的刪削指令。帕斯捷爾納克無法接受,並在義大利出版機構的幫助下率先出了意文版。雖然蘇聯當局十分惱怒並在此後脅迫帕斯捷爾納克放棄諾貝爾文學獎,但是一部完整的作品遠比任何獎項更有意義。我的小說《絕育》寫完近十年,在大陸沒法出,只是與臺灣秀威出版公司聯繫之後才有機會面世,才能免遭刪削之災。
難道臺灣之於我,不像義大利之於帕斯捷爾納克嗎?
絮絮數千餘言,以為序。
【論自由】這不是個新鮮話題。但是,只要對它進行哲學思考,就會不斷地發現新意。曾幾何,自由作為一種主義是中國政治語境中的大敵,故而「反對自由主義」冒濫為光輝一時的政治哲學命題與篇章。曾幾何,自由被看做一種政治化學,它的「化」被賦予了階級性,「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成為一場血腥的伏筆。自由是一種主義不假,但是,它被賦予階級性之後,帶來的不僅僅是血腥,更是深度的無知,從而使政治陷入一個奇怪的悖論之中―因為你無知,所以你暴虐;因為你暴虐,所以你更加無知。自由的含義太廣闊,以至於我們不得不從極其微小的塵世細節中去發現它的特性。比方說,一個高傲的女人的自由,它可以藐視帝王。帝王可以征服天下的土地,讓飽受其搶掠的敵國舉國跪在他的坐騎之下山呼萬歲。但是,即便他把那個要征服的女人一千次地壓在身下,那個女人的心也不會屬於他。你可以征服目力所及的世界,卻不能征服一個女人的心。這不是帝王的悲哀而是自由的偉大。我們設想的這個女人,一個歷史細節的象徵,有著她外界無法測知最底線的自由:她可以把佔有欲極強的帝王想像為她初戀的情人,一旦雲雨事畢,她還會冷對帝王。奴隸是不自由的象徵。奴役,作為一個辭彙,和自由也是對立的。但是,奴隸也有他思考的自由。所以,斯巴達克斯在無數次思考之後,決定用角鬥士的勇氣來反對殘暴的羅馬帝國。思考的自由與反抗的自由密切相連。一切凌駕於自由之上所謂集體道德,不過是一小撮人的謊言。他們編造意識形態謊言的結果是謀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一旦他們的利益得不到實現,或者別人的自由成為他們無知的威脅,那麼,謊言也不必多說,暴力隨之而來。暴力加謊言,是一切與自由為敵的無知兼無恥的勢力們的鎮宅之寶。上帝,賦予了人自由意志。我們可以選擇智慧,可以知道羞恥,儘管我們擺脫上帝規範的代價非常之大。但是,在此之後,上帝還是和我們繼續博弈。當上帝有意識地進行新一輪針對我們的智力博弈時,我們發現:人,確實更進一步地遠離了邪惡,儘管邪惡無法清除,甚至無需清除。我們知道了地球是圓的,是思想自由的結果;我們知道地球並不是宇宙的中心,其實也賴於我們相對於上帝的自由。深刻地思考自由的含義,我們才能理解―牛頓自由思考,發現萬有引力之後,何以看似矛盾地感謝上帝。我所說的這點幾乎與宗教無關,而且作為自由主義分子,我本能地討厭宗教狂熱。我說的是政治哲學或終極的道德哲學,而我的道德理論從來就沒沉沒在自由意志之下。如果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還是自由的內容之一的話,那麼,我就說:我的自由最後的價值就是摧毀一切假道德之名而行的無知與暴虐。無知與暴虐可以踩住我的頭顱,也可以打得我違心地求饒,但我永遠是那個有著自己追求的「女人」。我不在乎你是如何把我壓在身下的,但我身上的只是你的肉身而無你的靈魂。這個邏輯就是自由對無知與暴虐的最好報復!自由,存在於現實世界之前,首先存在與我們自己的內心。我們無法選擇歷史,卻可從中自由地選擇學習的榜樣。這是魯道夫‧沙澤曼的感想。我在他之外的發現是--即便你把我關在籠子裏,四周蒙上黑布,我還總有自慰的自由。我願意想誰,就想誰。權力控制,虛假的道德約束,對於我什麼都不是。我一點不下流,但是,我可以用相對下流的表達--羞辱你對自由的羞辱。問題就這麼簡單!
 打造成功有型的一流男人味:57招消...
打造成功有型的一流男人味:57招消... 詩情畫意說藥草
詩情畫意說藥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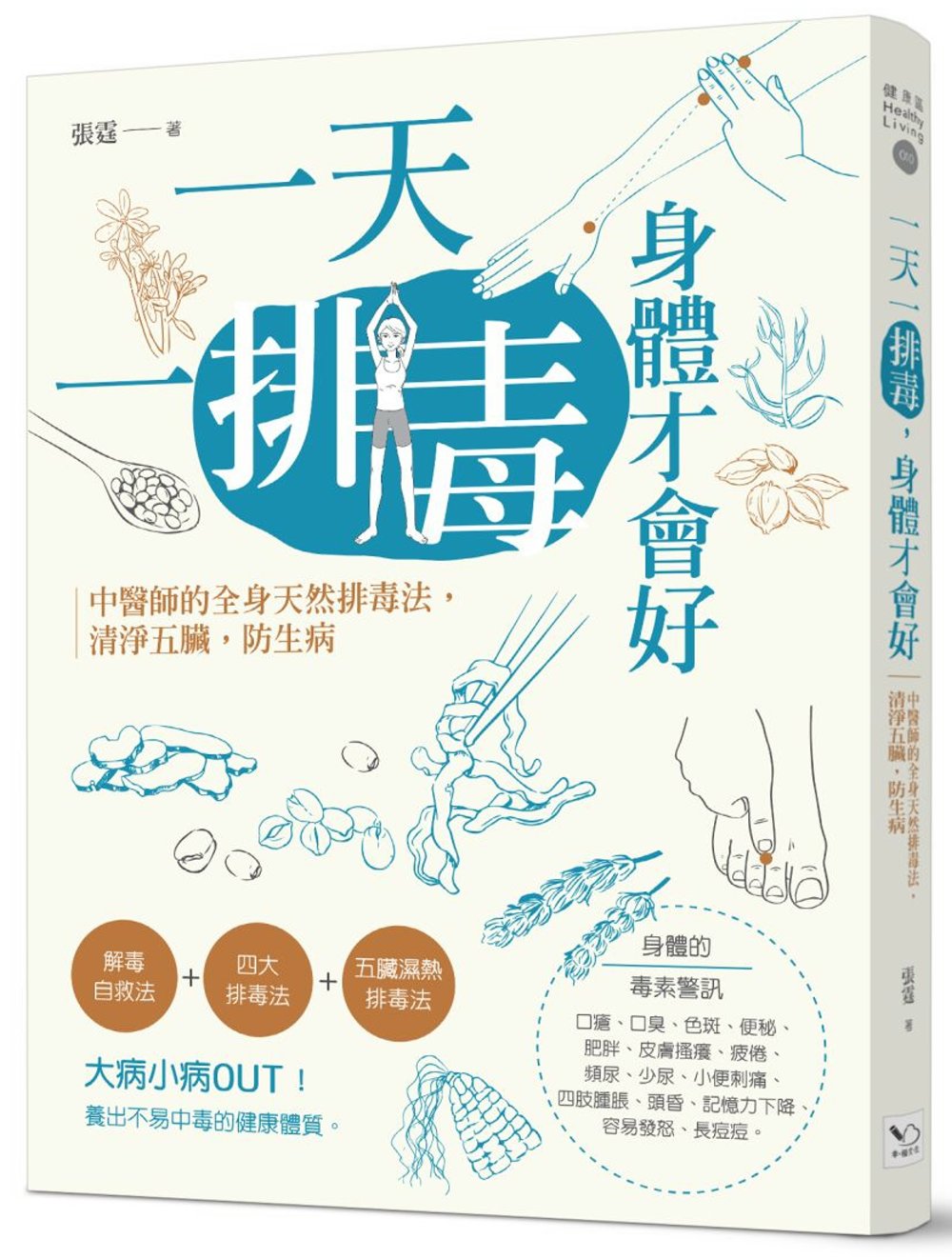 一天一排毒,身體才會好:中醫師的全...
一天一排毒,身體才會好:中醫師的全... 13億華人瘋傳神奇食癒力:101道...
13億華人瘋傳神奇食癒力:101道... 耳下按摩60秒,流口水消病痛:0到...
耳下按摩60秒,流口水消病痛:0到... 史上最完整營養素大圖鑑:14種維生...
史上最完整營養素大圖鑑:14種維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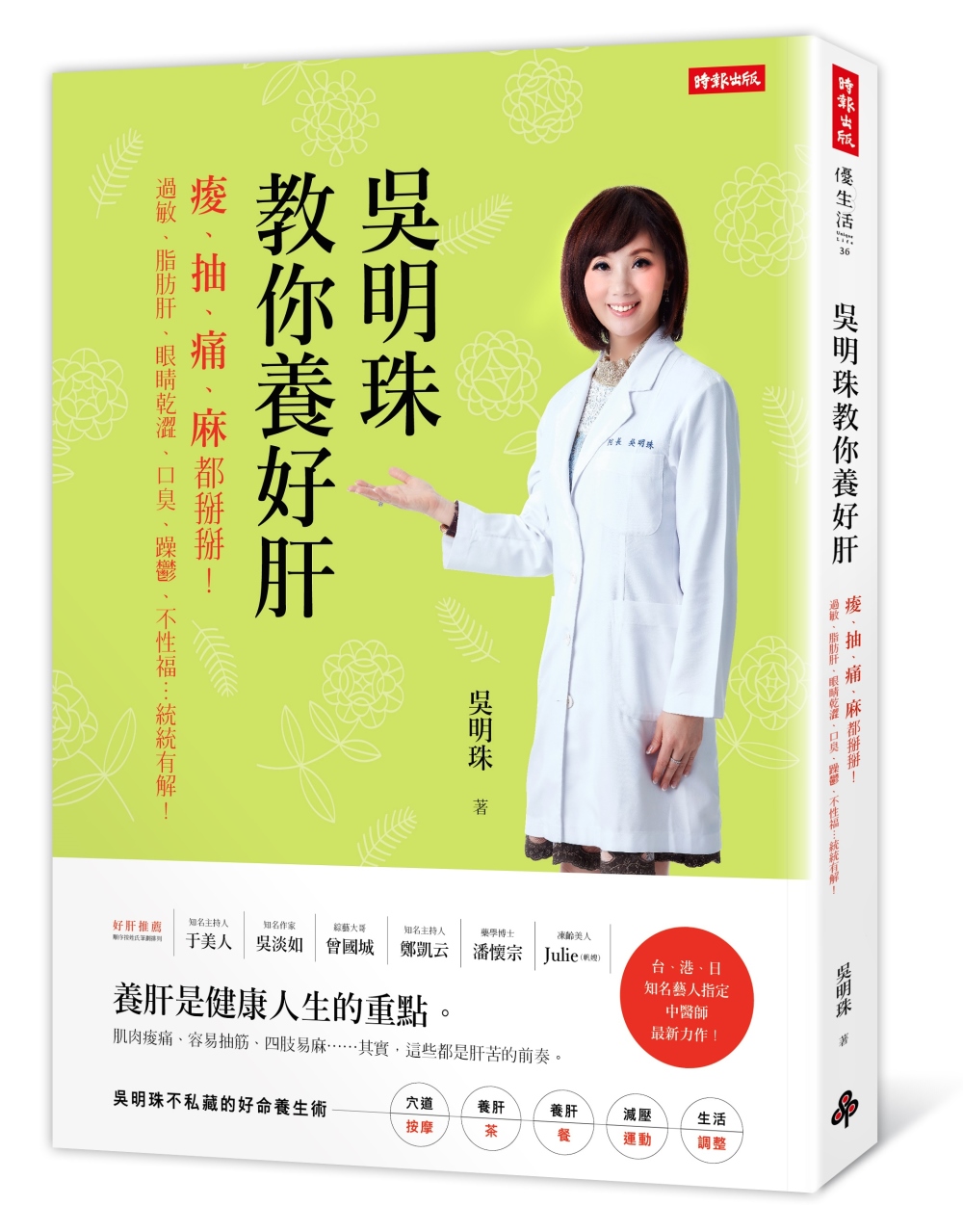 吳明珠教你養好肝:痠、抽、痛、麻都...
吳明珠教你養好肝:痠、抽、痛、麻都... 另類唐朝:用食物解析歷史
另類唐朝:用食物解析歷史 腸道保健家常菜
腸道保健家常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