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語:這次換我說給你聽 | 生病了怎麼辦 - 2024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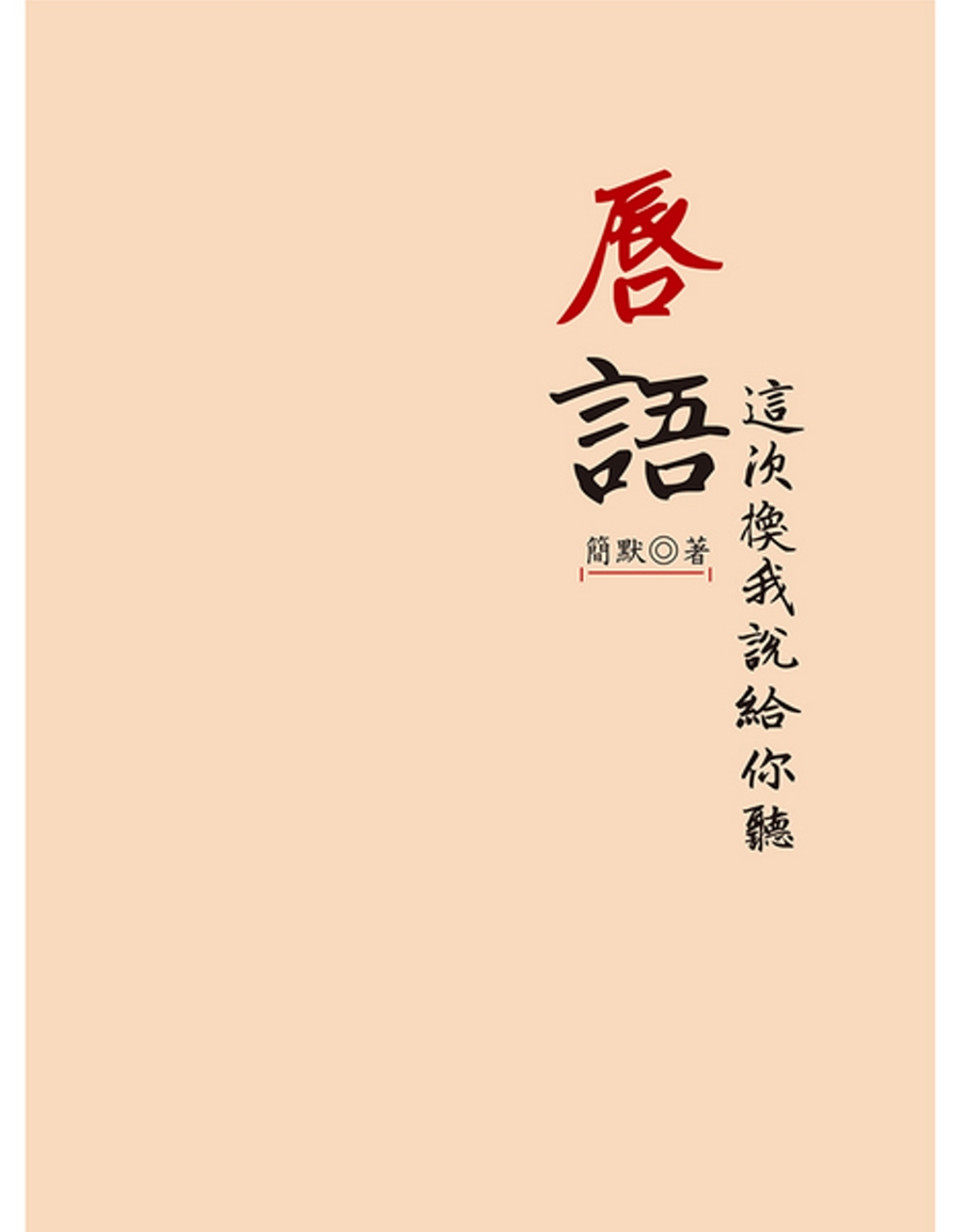
唇語:這次換我說給你聽
如果把這樣的依偎累加起來,
能把那些一次次的死去奪回來一點,該有多好。
這些年裡,不好好吃飯時,肚子偶而也叫,但最痛苦的,還是無法填補心中缺憾的孤寂感。
為了擁抱絕美的風景、嚐遍天下的美食、追尋無限的自由與歡樂、獲得至高無上的榮譽感,在路上背棄了一個又一個良善的靈魂。我們親手砌起了自己的獄,這是我們所處時代的悲劇。
有人為此感到喜悅,有人則感到惶恐,以為日子就這麼過下去了。
對作者來說,書寫是她的救贖,是解開枷鎖的鑰匙,她用無聲的語言對世界說出從未說出口的心意:我愛你。
重啟生命,走出內心城池,擁抱夢田裡最溫暖的顏色,我們學會含淚微笑。
本書中,作者帶領讀者進入她受文字救贖的祕密花園,由「凝視」「行腳」「家書」三部分組成,其中多篇作品曾獲獎肯定或被選載於重要文學期刊。
作者簡介
簡墨
中國作家、書法家,濟南市作協副主席,山東省書協會員,中國李清照辛棄疾學會理事。15歲開始在《詩刊》《人民日報》等發表詩歌,開設專欄,迄今發表400餘萬字。
輯一 凝視
他(她)們
卑微者
消逝的樹和麥田 3
放棄
樹
路上
遺物
他(她)沒有……
老粗布
為藝者
我的樹
輯二 行腳
失去
老街道
聽泉
靈岩寺
柔軟的濟南
看山筆記
濟南四季
新大明湖一角
在濟南看黃河
後光
尋找晏嬰
桃花城記
在植物中間
穹頂
輯三 家書
月光光,照地堂
那些永遠不能知道的
您知道我們從來不曾遠離
媽媽,我們永遠在一起
媽媽好像花兒一樣
每逢佳節
鄉村的母親那不死的人
後記
序
懷念娘
——在第五屆「漂母杯」全球華文主題散文大賽頒獎會上的答謝辭能獲獎,十分意外。這麼多人參與,萬眾矚目,知道會中高手如雲,大家也很多。還是覺得,我是個「新手駕車」,想過可能能獲得三等或優秀獎,但萬萬沒想到可以拿到一等獎。
感謝所有為此次大賽忙碌了一年多的人們,感謝您們!
《鄉村的母親那不死的人》來自我的一本散文集《唇語》,那本書還沒出版,卻是我自己最重視的作品之一,是用無聲的聲音對著世界說出的心意。此刻,我相信,我的母親,劉紹梅和劉瑞芝,也正在您們中間,看到我的口形,辨認著那三個字:我愛你。
在她們生前,我沒能說出這句話。在她們身後,我願意用餘生來說這句話給她們聽。
是的,我自己的母親和婆婆,都已走了。自己的母親在八年前,婆婆是去年。
有過痛不欲生的日子,有過自艾自憐的日子,想著從此徹底成為大地上飄著的孤兒,從此再沒有了故鄉沒有了家,沒有了暖暖軟軟的懷抱、沒有了那樣毫無條件、毫不要求回報的愛撫——愛情嗎?愛情是要求回報的,不回報,會恨,會怨,會漸漸冷淡。只有母愛,只有母親那個人,不會。你小時的屎尿她不嫌臭,你難看你膽小她更心疼,你青春期叛逆只彈吉他不學習吵她鬧她她統統包容,你失戀你找不著物品她急得像個神經病……只有母愛從你生到她死、濃度始終百分百、溫度始終攝氏一百度……母親是神。
就是這個「神」,她會死。如果不出意外,她會死在我們前面。當然,如果我們死在她的前面,她會有三條路可走:一、等於死去——一輩子在人背後偷著哭泣,慢慢煎熬;二、因煎熬而早死;三、或乾脆想不開,藉著一根繩子或一把安眠藥,追隨我們而去。她一生也就那樣了。我們卻總不能做到——我們也會難過,然後,不管難過多久,也許一生都不會完全恢復失去她的創傷,但我們還是能最終過我們正常的日子。記得一部老電影的話:「只有娘疼孩子,哪有孩子疼娘的?」這話誇張,卻也客觀,讓人灰心卻無可奈何。
她老年癡呆了都會記得我們的生日,她就算在死去之前的那一刻,還焦灼地望著守了一整夜的我們——我。那幾個月,我們每分鐘都在咳嗽、吐口水,需要隨時擦嘴角,當時我的眼睛不時困得闔上,再一下子睜大,繼續擦。在我們的那個淩晨,她對揉著倦眼來換班的哥哥說:「孩子,快來,叫孩子歇歇!」這居然就是她的遺言。她跟死神抗爭一夜,也許就為了說出這句非常可笑、非常無意義的話。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只看到,她說完這句話,就昏迷過去,再也沒醒來。
我們對她的孝敬無非是在最後集中時間陪伴了她五個月。對於婆婆,那個母親也是,對她的孝敬無非是每年來我這裡過冬——這裡有暖氣,比鄉下暖和。在我寫「中國文化之美系列」最著迷的那幾年,總是匆匆為她和孩子準備好飯食,就繼續寫作,不吃不喝。創造的幸福讓人不可自抑。我能迷迷茫茫感覺到她來過書房,再悄悄出去。好幾次,焦灼的眼神燙到我,可娘她一直沉默,直到一隻筆「啪」掉到地上,才突然闖進來,幫我撿起,開口說話:「妮兒,你這樣,我心疼!」我抬頭,看到了娘滿眼的淚。……我們總是接受而不是施愛給我們的娘,我們總是讓她焦灼。我們愧對我們的娘,無論她活著或是死去。
我們的娘,以及我們的兄長和姐姐的、甚至我們的叔叔和阿姨的、我們的娘,是最後一批最受苦的娘——她們不像現在的娘,只有一兩個小孩,她們一般不少於兩個小孩;她們大都出自鄉村,即便後來她發奮求學,在上世紀四〇年代、五〇年代、或六〇、七〇年代考上大學或者被保送學員,卻總是根在鄉村,要照顧鄉村的婆婆和自己的媽媽,有時還要照顧婆婆的婆婆、媽媽的媽媽……她們挨過餓、甚至挨過鬥;她們很少能特別有出息有大成就的,因為她們太難太苦,拖累太多也太疲憊……她們就這麼死了,大部分都已經死了。她們中還活著的,我們使勁祝福她們。
這個年代,需要勵志需要「懷念狼」,很好,也很必要,但也有必要回頭看看來處,懷念娘,從而感受感念感恩我們的娘,讓世界由此延續人間最美好的情感和最美好的德行,讓母愛和母愛似的大愛普照萬物,讓娘成為我們、成為萬物的一部分,讓我們和我們的娘——永、不、分、離。
(本文發表於《天涯》二〇一四年第六期,題目為《農婦們》)
他(她)們 第二章:寓言 這一組,寫鳥兒。 好久了,不記得了他(她)們的來處,似乎來自我的夢境。你把它看成真的也沒什麼不對。 因為面對人群,我有時羞澀,期期艾艾講多好。 不複雜,這記述只是適度惆悵而已。 但請耐心傾聽,他(她)們的哀鳴。 † 姑娘的歌唱 要說的這隻鳥兒像人。 她的鳴叫像歌唱。 七個音符,抑揚頓挫,組成一個音節(當然,還可以顛來倒去反覆變化,以至無窮),婉轉得如同一個姑娘的歌唱。裡面有一個最高昂卻柔美的音符,是最好看的、畫龍點睛的那一「點」,小提琴協奏裡最動聽、最矜持的那一個。 當然,如果你是女的,願意把這聽成一位年輕人不停口的口哨聲也可以。 她有著修長的、蓋世無雙的五彩尾巴——簡直就是孔雀的,如假包換。同時呢,與木框一樣黑的,是她的頭上羽毛;雪一樣白的,是她身體兩側的羽毛;血一樣紅的,當然是她乖巧的嘴唇,哦還有,粉紅的小腳掌……唉,是個白雪公主耶,鳥類裡的白雪公主耶。 她多麼愛歌唱呀:清晨,她停在枝頭,唱,薄脆;黃昏離巢,唱,迷離;上午練習飛翔的時間,唱,清越;下午學習柔美舞步時,唱,優雅……唔,她還沒有戀愛過,不曉得到那時,她的歌喉會不會甜蜜得夜夜放光華呢? 然而,獵人來了。 當然,獵人裡也是有心軟的。她的幸運在於:她碰上了這一種。 他常常靜靜聽她的歌唱。開始時,她甚至還有些靦腆,有些躲閃。後來,每當看到他,看到他專注的眼神,她的歌唱就更加悠揚。當然是多麼難多麼巧地遇了知音。這多好!比吃到好吃的蟲子還要好上一千倍。 她沒有被子彈擊傷,只是被網子捕捉。她甚至有些心急、心甘情願地跳進他的網子裡。 她被這個好獵人——好獵人也是喜歡她的絕美歌聲而吸引得不得了呢——帶回家。 她被放在一個極其漂亮的籠子裡,每天有精良的小米和水甚至牛奶侍奉著。 她不曉得要被關進這麼小的地盤。但她多麼柔順,並不是好挑剔的鳥兒,總能忍下來。還自己找些好理由,使自己想開。於是,雖然她沒有了枝頭,卻還是歌唱。 只是,音節裡少了那個最高昂卻柔美的音符。像畫龍點敗了眼睛,沒有了神氣;像小提琴換成了大提琴,沒有了活潑。 自由和歡樂這些隸屬奢侈品的東西可多可少,乃至可有可無。她習慣做成「大提琴」已經好多日子了。
 天天好心情:巴曲花精情緒密碼
天天好心情:巴曲花精情緒密碼 龍族英雄〔狴猂〕:駛向地獄的列車
龍族英雄〔狴猂〕:駛向地獄的列車 國小閱讀與寫作指引<6年級>上冊
國小閱讀與寫作指引<6年級>上冊 迎面闖關:闖過關卡,缺陷就不再是缺陷
迎面闖關:闖過關卡,缺陷就不再是缺陷 語言病理學基礎(第二卷)
語言病理學基礎(第二卷) 母乳最好(暢銷回饋版)─哺餵母乳必備指南
母乳最好(暢銷回饋版)─哺餵母乳必備指南 等待&希望(公益紀念版)
等待&希望(公益紀念版) YES! 我把牙齒變白、變美、變健康了!
YES! 我把牙齒變白、變美、變健康了! 我的世界,自己定義!:75位千禧世...
我的世界,自己定義!:75位千禧世... 等愛的天使
等愛的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