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與哀愁的道程 | 生病了怎麼辦 - 2024年11月

愛與哀愁的道程
「我的前面沒有路
我的後面都是履痕路跡⋯⋯」
回想錄、智惠子抄、山之四季,
日本現代美術、現代詩開拓者
高村光太郎的藝術、愛情、美學。
「高村光太郎低調、謙卑、邊緣、無目的,僅僅帶著良善、敬畏之心,守護本我的星火,以純真與夢想無意間為世人構築了一個可以喘息、修補、獲得慰藉的平行宇宙。」——吳繼文(作家、譯者)
日本著名雕刻家、畫家高村光太郎,不僅是日本近代美術的開拓者,也是日本新詩史上無法抹滅的名字,書寫與妻子智惠子的「愛的編年史」——《智惠子抄》,尤其被推崇為世界文學珍品,廣為世人傳頌,而智惠子死後,彷彿隱士的高村先生則展開了自然寫作的新頁。
一九一一年,二十八歲的高村光太郎結識女畫家長沼智惠子,三年後發表了第一部詩集《道程》。一九三八年,不敵病魔(精神分裂症),五十二歲的智惠子死於肺結核,高村光太郎出版了紀念詩集《智惠子抄》,見證兩人橫跨三十年的愛情。晚年,他獨居於岩手縣的山間小屋中,自耕自食,並寫下了許多山居隨筆。
本書彙集高村的《回想錄》、《智惠子抄》,以及《山之四季》,除了提供讀者一窺高村光太郎藝術的養成,與智惠子的愛情,以及隱居山林後對生活美學、哲學的思考,更認識一位終其一生追求純粹的人。
作者簡介
高村光太郎(1883—1956)
號碎雨,日本近代著名雕刻家、畫家和詩人。出身於藝術世家,父親高村光雲。早年前往西方遊歷,學習雕刻,歸國後正式開始詩歌創作。初期醉心於「頹廢藝術」,後投身於白樺派和民眾詩派的文學活動,是日本新詩運動的重要人物,被譽為「日本現代詩之父」。著有詩集《道程》、《智惠子抄》、《典型》等。
譯者簡介
吳繼文
作家、譯者、出版人,著有長篇小說《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天河撩亂》,譯有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記》、井上靖《我的母親手記》、藤原新也《印度放浪》、中平卓馬《為何是植物圖鑑》、南直哉《直面生死的告白》、野々村馨《雲水一年》,以及吉本芭娜娜《廚房》、《蜥蜴》等多種。
回想錄
智惠子抄
山之四季
附錄:略年譜
譯後記
譯後記
吳繼文
翻譯是必要之惡,尤其是詩。
古代翻譯佛經,由國家提供人力、物力資源,網羅海內外精英,集體作業,譯場組織完備,設有譯主、筆受、證義、潤文、校勘等,細分甚至到十幾種職務,以其審慎程度,應該沒有什麼不能解決的翻譯問題,結果還是有所謂「五不翻」。現代譯者自己就是一座譯場,而且還沒有「不翻」的紅利,遇到以用字精鍊、意在言外為尚的詩,咬文嚼字起來還真是「撚斷數莖鬚」不止,到最後仍充滿不安,深恐愧對作者。因而在體例上盡可能忠於作者分行斷句與順序、標點有無、分段與否,並尊重作者語意、意象及其時代語感。
內文中若括弧內容為作者原文則字體大小不變,若為譯者所加則縮小字體以示區分。長度、面積、容量等依照明治二十四年頒布、昭和二十六年廢止的「度量衡法」,比方一尺約三十公分,一間約一·八公尺,一町(六十間)約一〇九公尺,一里(三十六町)約四公里。
〈回想錄〉及〈山之四季〉的「花卷溫泉」篇,文末均註明為「談話筆記」,內容難免略顯鬆散、蕪雜,但也如實映現當年的世相,前者如人鬼雜處的舊江戶城下町生活繪卷、庶民驅魔去邪的萬應良方「九字護身法」,後者如男女混浴風情、「又鬼」傳說等,彌足珍貴。只有細節才能讓曾經活生生存在的人們,以及僅僅屬於他們的時間和空間再現莊嚴,因為無可取代,也難以複製,不被輕易付諸南柯一夢。
《智惠子抄》以一九五六年新潮社的新潮文庫版為底本;《山之四季》以同年發行的中央公論社版為底本。
◆
我的前面沒有路
我的後面都是履痕路跡
啊啊自然喲
父親喲
讓我獨立於世的廣大無邊的父親呀
請時時刻刻守護著我吧
願父親的魂魄總是充滿我身吧
為了這迢遙的道程
為了這迢遙的道程
這是有獨立蒼茫之感的〈道程〉,光太郎最膾炙人口的一首詩,短短九行,收在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由抒情詩社出版的同名詩集《道程》中,它的原型,則是刊登在當年三月五日發行的《美的廢墟》雜誌第六期上,長達一〇二行的〈道程〉。短期間內進行大規模的刪削,彷彿可以看到光太郎作為江戶木雕職人傳承者的潔癖:收放有度的飽滿,以及對贅肉的零容忍。
長版〈道程〉多方面鋪陳類似的孤絕心境,捕捉了生之靈光乍現的一刻:「我總是佇立在路的盡頭」,而唯一信靠如父的大自然,竟然只是微微一笑即鬆開它的手,隱沒在永遠的地平線彼方,一開始我驚惶如棄兒,然深吸一口氣後,卻清楚感受到作為一個赤子的使命。
◆
光太郎從木雕職人的正統訓練出發,父親光雲又是一代巨匠,他可預見的平穩、安全、理所當然的路早已被決定,但歷經紐約、倫敦、巴黎藝術與文學的刺激,尤其是充滿活力的庶民生活之洗禮,枷鎖頓獲解放,深感作為一個小寫的人之自由與尊嚴的可貴,回首來處,那個遠方的保守國度何其蕭瑟,劣等感油然而生,甚至強烈自我嫌惡,原先十年的遊學/藝術武者修行計劃,不到四年即戛然而止,如道元禪師當年靈光乍現(或云「開悟」)獲師父如淨印可,落拓離開寧波天童寺「眼橫鼻直,空手還鄉」,光太郎想回去做一場典型的對決(典型vs.典型)。後來他有一本詩集就叫作《典型》(一九五〇)。光太郎和道元都用他們之後人生中的所有作為,向世人證明那乍現的靈光,或者說開悟的真實內容。
有一陣子光太郎淨雕些木刻小品,如鯰魚、石榴、蟬或白文鳥,試圖用最唾手可得的事物揭示何謂雕刻性,為什麼桃子有而蘋果沒有;有意義的作品不是惟妙惟肖、纖毫畢露的寫實,而是自然動勢 (mouvement) 的有無。但雕刻無法完全滿足他表現上的慾望, 如果不將此欲望用文字表現出來,勢必轉移到雕刻之中,讓雕刻成為文學的附庸,於是為了維護雕刻的純粹性,他大量寫詩。雕刻性也好,雕刻的純粹性也好,在日本的創作者要嘛從未意識到,或者知道也不在意的東西,卻是光太郎的念茲在茲。
◆
世人常說個性決定命運,但光太郎只是放下揀擇,像個一無所依、未被定義的赤子,堅守求道的初心,無悔地而行,活在真實中——不是普世的真實,而是看住此時此刻,堪忍背負命運牢籠,在一切不自由與敵意之中,仍堅持「蝗蟲的尊嚴」(卡爾維諾形容色諾芬《長征記》中一路敗北卻謹守城邦文明法則從波斯經小亞細亞無傷回到故鄉的一萬希臘傭兵),做自己的主宰,因而擁有的一切自由。或許有些孤傲,而更多的是承擔。他拒絕教書,放棄家業,錯位而出,自我流放於每一條路的盡頭,和完全信賴他的智惠子成為兩人世界的「同棲同類」,貧無立錐卻有充盈滿溢的理想與愛。智惠子的天真無邪淨化了他,但智惠子的知覺失調與死亡,現實的敗北,最後還是讓光太郎走到了愛的盡頭,只能回歸如父的自然,在荒僻的鄉野獨居自炊,度其餘生。
然而光太郎也是一個美麗的失敗者。在這個被瘟疫——疾病學上的瘟疫,或者(全球化、追求數量、歌頌成功、讚美勝利的)貪婪的、傲慢的瘟疫席捲的時代,他低調、謙卑、邊緣、無目的,僅僅帶著良善、敬畏之心,守護本我的星火,以純真與夢想無意間為世人構築了一個可以喘息、修補、獲得慰藉的平行宇宙。
他晚年的大作,是如今樹立在十和田湖畔的《裸婦像》——以記憶中的智惠子為原型,兩位相對而立、上身前傾的裸婦,面容平靜而貞定,左手曲肘,平舒五指,手掌向前,與對方似觸非觸,於無盡的時間中流轉,山林、湖水、雨或雪、榮與枯、喧囂或空寂,彷彿大自然恩慈呵護下的鎮魂之詩。在佛教中,這樣的手印稱之為「施無畏」。
回想錄 (節錄) 二 我小時候體弱多病,父母為了養育我煞費苦心。我們家的小孩,最大的是姐姐咲 (Saku), 其次是梅,接著是我,後面有一個叫靜的妹妹,然後是道利和豐周。再下去有一個弟弟叫孟彥,後來成為藤岡家養子。之後還有一個妹妹佳。 這些姐弟妹間,只有最上面的兩個姐姐在年紀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到我出生之前,母親連續生了兩個女兒,如果生不出繼承家業的兒子,以當時的習慣隨時都有可能被趕回娘家,所以覺得很焦慮。母親曾告訴我說:「小光在我肚子裡的時候,覺得這次如果生的還是女兒就說不過去了。所以到處去求神拜佛,希望無論如何賜給我一個兒子,最後終於如願。小光出生時,爺爺說『阿豐啊,成功了』,我從沒那麼快樂過,就像登天了一樣——小光真是我的幸運兒!」因為這樣,我被當作寶貝一樣照顧。祖父他們則認為我是神佛所賜,對我疼愛有加。 我六歲入學,但五歲之前我完全不會說話。長輩們都擔心我會不會是個啞巴。醫生認為是小兒驚風,很快就會開始講話,不要太過擔心,然後有一天早上,頭上突然冒出了膿疱。以前的醫生覺得出膿疱是好事,反而很正面看待這樣的事,只要膿疱一治好,馬上會開始講話。或許是言語中樞發生了什麼障礙吧。果真之後很快就開始講起話來,等上學後都沒什麼問題。 母親不會對我說教,唯有對我講話的遣詞用字要求很嚴,總是不厭其煩地糾正我。在學校難免會學其他同學的用詞,回到家不小心脫口而出,一定會叫我改過來。今天已經沒有所謂江戶話了,也不知道正確江戶話的基準是什麼,但過去好壞是可以清楚辨別的。祖父對怎麼講話也是很囉嗦,一旦聽到我說話有不得體的地方,就會罵我「切,講話像個鄉巴佬,不成體統」。我被禁止的用語中,態度傲慢或粗魯輕率的話最多,所以也等於是關於品德良心的訓誡。所謂說好話,還包括言之有物。到今天我寫文章的時候,就會想起母親的訓誡,發現對語感的表現幫助很大。其中有很多絕對不容許的用法,當我寫詩時即會無意識地受到影響。常常有些很想使用的詞彙或表達方式,卻不得不塗掉改寫,都是因為母親的教導變成我本能一部分之故。從我自己的經驗看來,以遣詞用字來進行教育是非常好的方法,語言的訓練對今後的人們還是很重要。
 戰國諸葛.竹中半兵衛:黑田官兵衛終...
戰國諸葛.竹中半兵衛:黑田官兵衛終... 潛伏的暗殺者-肺結核 [精裝]
潛伏的暗殺者-肺結核 [精裝] 人間失格【精裝典藏版】
人間失格【精裝典藏版】 抗疫防癆山海間:東臺灣防疫先鋒李仁...
抗疫防癆山海間:東臺灣防疫先鋒李仁... 雪國(川端康成 諾貝爾獎作品集1)
雪國(川端康成 諾貝爾獎作品集1) 新編古典今看
新編古典今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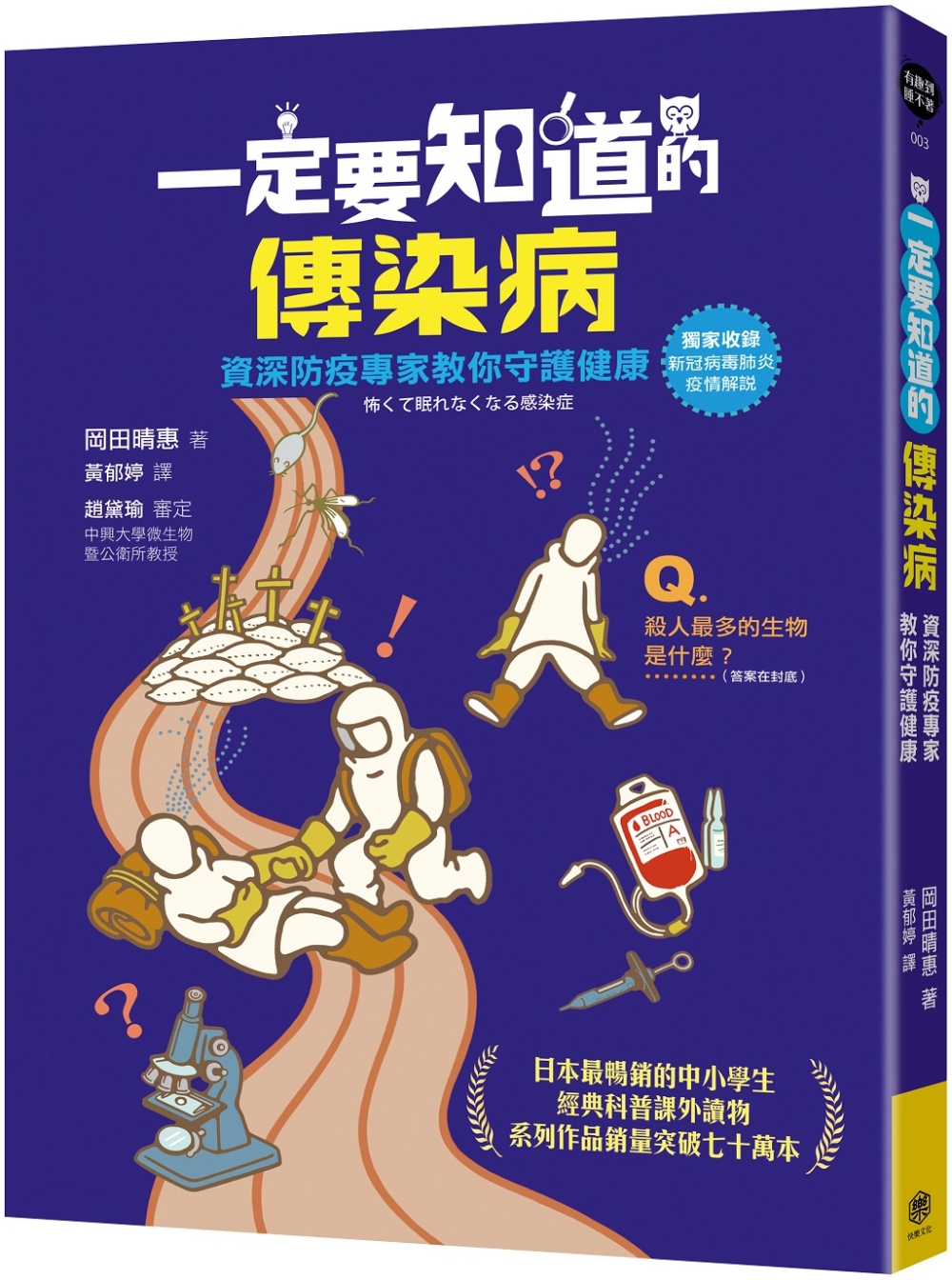 一定要知道的傳染病:資深防疫專家教...
一定要知道的傳染病:資深防疫專家教... 解讀攝影大師:認識他們的創作人生、...
解讀攝影大師:認識他們的創作人生、... 肺結核大反撲的自保之道
肺結核大反撲的自保之道